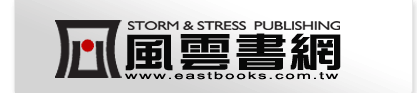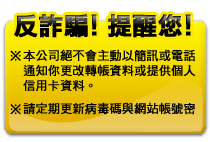※ 【序】
歷史,在轉捩點上 龔鵬程
觀乎人文,察於時變
「江聲不盡英雄恨,天意無私草木秋」,歷史的驚濤駭浪,翻翻滾滾。奔騰處,激越慷慨;低回處,幽咽纏綿。但是,游動波流,卻徒然教人悲喜莫名、棖觸萬端,而不能知其究竟。
到底歷史只永遠表現為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,還是發展成無窮無盡的追尋?一切變化都歸於既定的人類使命,還是它在變化中帶領我們攀上幸福的頂峰?文明的驟起驟衰,猶若潮汐,人類的生涯有限,又怎能探勘歷史的跫音、尋找文化的座標?暗夜長途,何處才是歷史的光明?忽焉就死,歷史對人生的意義又在哪裡?
任何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,都是相當惶惑茫然的。歷史,常像雅士培(Karl Jaspers)所說,不時表現為一團烏七八糟的偶然事件,如急轉的洪流,從一個騷動或災難緊接到另一個,中間雖有瞬間出現的短暫歡樂,亦如小島一般,終究也要遭到吞沒。但有時,歷史也並不全然如此盲亂,它彷彿如康得所說,是一種明智計畫的理性過程,並不斷趨向於成熟完美──雖然他也承認整個人類歷史之網,是由愚昧幼稚的虛榮、無聊的邪惡、破壞的嗜好所織成。那麼,歷史到底是什麼?歷史中是否確能找到明顯的因果關聯或變遷的規律呢?
這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事。我們傳統的史學,大抵總相信歷史的道德趨向,王道理應成功、霸道終歸失敗,暴君一定亡國、仁者當然無敵。歷史的道德規律,推動著歷史的發展,所謂「天有常度,地有常形,君子有常行」(東方朔《答客難》)。西方自奧古斯丁(Augustine)以降,亦輒欲說明人類歷史乃遵循一種形而上的律則在進行著,一切皆為上帝所安排,個人的遇合、國家的治亂,乃至於皇權之成立,都決之於上帝的旨意與恩寵。十八世紀以後,因受科學發展的影響,認為人性與物理都須受自然法的支配,一切都決之于理智,而既以理智為依歸,則人類即必須珍視自由,不自由,文化必定衰落。十九世紀後,又由於達爾文學說的影響,相信人類的歷史一定是步步前進的,不管分成若干階段,後一階段總要比前一階段好些。另一派則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歷史循環說或週期說,諸如「天下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」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「五德轉移,治各有宜」之類,與西方思辨性歷史哲學亦多有暗合者,其言甚為繁賾。這些主張,雖各有論點,但總都具有決定論傾向,不認為歷史只是盲目的、偶然的聚合,故努力地想在歷史的變遷中,抽絲剝繭,爬梳出一個規律的模型,以掌握歷史的動態。不幸的是,歷史事件之雜亂無章、龐然紛若,歷史知識之性質特殊,往往使得這些規律在解釋時遭到困難。所以自十九世紀蘭克(Ranke)及普魯士歷史學派提倡經驗的史學以來,黑格爾式思辨性的歷史哲學即逐漸式微了,近代實證論及行為主義者,甚至都曾排除對歷史之意義的追究。但是,這也是矯枉過正之談,因為追問歷史的意義,不僅是一種合法的(legitimate)探索,而且是我們非做不可的事。故奧古斯丁這個傳統,在當代又漸有再生的趨勢:梅耶霍夫(Meyerhoff)所編《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哲學》中,曾列舉Berdyaev(柏提耶夫),Barth(巴特),Niebuhr(尼布林),Tillich(蒂利希),Butterfield(巴特菲爾德),L öwith(洛維特)等當代思想家,來證明這一點。
糾纏於這些傳統、質疑與趨勢之中,歷史,依然曖昧難明。那裡面,自不乏小樓聽雨、深巷賣花的款款情致;那裡面,也總含藏著鐵馬秋風、樓船夜雪的莽莽蒼蒼。英雄叱吒,遺民淚盡,千古興衰,一紙論定。歷史的浩瀚博大、莊嚴深邃,實非此類爭辯與追詰所能窮盡。每當我們仰觀蒼穹,列星燦燦、浮雲皓皓時,便自然而然地會興起這種充脹胸臆的歷史感情,思而不見,望古遙集,歷史的呼喚,於焉展開。
就是在這樣的呼喚與感應中,歷史才對此時此地的我們具有意義,而我們也才能真正進入歷史中,去「觀看」歷史的動態,稽其成敗盛衰之理。不管歷史是理性自主的運作,是隨順理性的計畫安排,抑或只是受到盲目意志的撥弄,既無理想目標,也無法則,我們觀察歷史的這個行動,本身就具有省察人類存在之歷程的意義。而這種省察,也內在地開展了我們的世界,讓我們超然拔舉於此時此地之上,開拓萬古之心胸,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這不是遁世逃避,乃是積極開拓自我,並借著這樣一種活動來跟現實人生社會做一番對照,以「察盛衰之理,審權勢之宜」(賈誼《過秦論》)。換言之,歷史縱使只是一條惡魔遍佈的價值毀壞之路,觀看歷史,依然可以讓我們更清明地向理性與道德的完美境域邁進。
這也就是說,歷史的性質與功能,它所能提供給我們的,其實就在我們觀乎人文、察於時變的行動中。人文的發展、價值的探索、社會的變動、人類一切理性與非理性的成就,俱在歷史中向我們招手,並展露它廣袤繁多的姿容。只要我們真正涉入其中,歷史立刻就進入了我們的生命,使我們能通古今之變,參與歷史的脈動。
歷史遺忘了中國,中國也遺忘了歷史
古今之變,到今天可說是劇烈極了。
明朝末年,利瑪竇來華傳教時,他所繪印送給中朝士大夫的《輿地全圖》中,因為中國並不在中央,以致引起許多批評,《聖朝破邪集》裡甚至攻擊他:「利瑪竇以其邪說惑眾。……所著《輿地全圖》……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。……試於夜分仰觀,北極樞星乃在子分,則中國當居正中,而圖置稍西,全屬無謂。」(卷三)這時,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與文化,還是充滿自信的,他們所表現的文化內容,也能讓耶穌會遠人欣然嘆服:認為在世界各國仍處於蒙昧之時,中國即已有了孔子,孔子與基督有相同的神性與使命,是「真的神」;而儒教基於相愛之關係所產生的政治制度,迥異於西歐基於主人與奴隸的關係,對西歐社會,更為一優美之對照,要改造西歐,即有「接種中國思想」的必要。
可是,不到二百年後,這種局面就完全改變了。在歐洲刮起的中國熱,逐漸冷卻,自十五世紀以來,基督教國家向「落後地區」擴展其文化的行動倒越來越熾烈。不僅有黑格爾這樣的大哲學家宣稱「所有的歷史都走向基督,而且來自基督。上帝之子的出現是歷史的軸心」;詩人吉卜林(Rudyard Kipling)也高唱「白人的責任」。所謂白人的責任,就是說白種人有責任「教導」有色人種,要他們採取西方的制度、西方的生活方式,並學習西方的技術。遠洋殖民和貿易事業,逐步把他們這種「偉大」的理想推拓到非洲、亞洲。利用船堅炮利,轟開了天朝的大門,搖撼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。
於是,夕陽殘照漢家陵闕,天朝的光榮,恍若西風中的枯枝敗葉。沉淪崩圮的世代、花果飄零的民族,這時所再呼喊的,便不再是歷史與文化,而是接種西洋思想了。受挫折的中國靈魂,從此被迫去擁抱另一個天朝,學習另一套歷史與文化,以重塑中國的未來,並理解中國的過去。
這當然是可哀的事。昔日的真神,現在概在打倒之列,歷史被當作包袱,視為與現代對立的僵化凝固體、阻礙進步的絆腳石。任何人在面對中國歷史時,都可以毫無敬謹謙撝之心,或莊嚴誠懇之情,都有資格恣意批判。很少人真正通過歷史的屬辭比事,以疏通知遠,卻大言炎炎,棄此歷史文化如敝屣。社會上一般人,對歷史更是隔膜,歷史知識至為貧乏,即使是高級知識分子,對本國史,亦輒有比鄰若天涯之感。
連橫曾說:「史者,民族之精神,而人群之龜鑑也。代之盛衰,俗之文野,政之得失,物之盈虛,均於是乎在。故凡文化之國,未有不重其史者也。」(《〈臺灣通史〉序》)章太炎也以為:「群之大者,在建國家、辨種族。其條例所系,曰:言語、風俗、歷史。三者喪一,其萌不植。」(《檢論》卷四《哀焚書》)這些,在今天大概都是不甚流行的看法。姑不論我們是否仍可稱為文化之國,也暫時不管當前社會名流是否皆以競作世界公民是尚,而恥言民族主義;倘若我們毫不諱飾地來看,自會發現目前我們對歷史的淡漠與無知,確實已經到了令人拊膺長嘆的地步了。
造成這種現象,固然肇因於這次天朝的大變動,勢之所趨,莫可奈何,但我們對歷史教育的輕忽與僵化,實也是一大原因。至少在制度上,大學分組的辦法,幾乎強迫一半以上資質穎異的學子,從高中起便視歷史為身外之物,從此不再接觸。少年時期,如此缺乏歷史的薰陶,長大以後又怎能奢求他們會有歷史的感受和理解?而等到整個社會上的成人都普遍欠缺歷史的認知時,又怎麼會尊重歷史?怎麼可能汲探文化的根髓?徒然讓兒童去肩負背誦《三字經》《唐詩三百首》的重任,就算達到歷史灌輸的目的了嗎?何況,歷史教育並非灌輸即能奏效的。現今歷史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,不能激發國民的熱情與嚮往,無法砥礪種性、激昂民氣,教材之平板僵硬,自屬重要癥結。須知讀史之要,在使人知政事風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,所謂「《堯典》可以觀美,《禹貢》可以觀事,《皋繇謨》可以觀治,《洪範》可以觀度,六《誓》可以觀義,五《誥》可以觀仁,《甫刑》可以觀誡」(《書大傳》)。我們的歷史教育,似乎對此仍少措意。
當然,可以告慰的是,在學術界、高等研究機構中,仍有不少傑出的學者在從事歷史之探索。但彷彿大家還不曾理解到:歷史,尤其是自己國家文化的發展歷史,並不只是一門孤立的學科,而是人存在的基石。人存在的意義,無不是根于歷史而展向未來的,過去的歷史傳統,構成了我們理解的背景。我們之所以能立足於世界,並向這個世界開放的唯一依據,仰賴的就是這個力量。這個力量一旦不顯,歷史就成了搞歷史的人的專職,成為紙面上的一堆堆資料,與公共大眾無關,而我們的研究與教學,自然也就僅能局限於平面事件的排比與介紹,不再致力於觀人文、察時變了。
但是,我們必須注意:當我們漠視歷史時,歷史也正在遺忘我們。
從前,四夷賓服、萬方來朝的時代,我們天朝對於四裔遠人及寰宇全貌,實在缺乏理解。而現在的天朝,也同樣沒有把「落後地區」算進人類的歷史裡去。像房龍那本名著《人類的故事》裡,你就幾乎找不到人類之一──中國人的故事。威那·史坦恩(Werner Stein)原著,貝納德‧古倫(Bernard Grun)和華萊士‧布勞克威(Wallace Brockway)英譯增訂的《歷史時間表》中所指的歷史,也不全是整個人類的歷史,而只以西歐、美洲為其重點。儘管印度、中國、日本等國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有記載,也非有意省略,「但作者們也沒有做任何努力來調查這些地區的歷史事件」(見該書序文)。
更有趣的例子,是羅伯特‧唐斯(Robert B. Downs)所寫的《改變世界的書》(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)。唐斯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,他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,有十六本書改變了世界,這十六本書是:一五一三年馬基雅弗利的《君主論》、一七七六年潘恩的《常識》、一七七六年亞當‧斯密的《國富論》、一七九八年馬爾薩斯的《人口論》、一八四九年梭羅的《不服從論》、一八五二年斯托夫人的《湯姆叔叔的小屋》、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、一八九○年馬漢的《海權論》、一九○四年麥金德的《歷史的地理樞紐》、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的《我的奮鬥》、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的《天體運行論》、一六二八年哈威的《心血運動論》、一六八七年牛頓的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》、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、一九○○年佛洛伊德的《夢的解析》、一九一六年愛因斯坦的《相對論原理》。
這些書,在我們《辭海》的「中外歷史大事年表」裡差不多都提到了,但是像《傳習錄》《四庫全書》之問世,卻不見於唐斯這份書單裡。當然,我們並不因此而否認這紙書單裡的書確實影響深巨,確實改變了人類的歷史,可是,這究竟是誰的歷史?那個也曾參與人類文明之創造、也曾貢獻世界歷史之開展的中國,難道就這樣被遺忘在歷史之外了嗎?
是的,天朝的燈影舞姿,正如是之璀璨,蜷縮在文化邊陲的荒煙蔓草中的我們,恐怕早已被剔除在歷史之外,置諸天壤若存若亡之間了。
然而,何必慨嘆,何用嗟傷,旁人本來也並沒有義務要熟諳咱們中國的歷史。而且,只要我們自己不遺忘歷史,歷史也必不遺忘我們。無人懷疑中國現在必須參與世界,必須接納西洋文化,可是假若我們再想想當年新文化運動諸賢如梁啟超、胡適等人開列「國學最低限度必讀書目」時,為什麼要說「並此而未讀,真不得認為中國學人矣」,就可知道歷史的認知,原無礙于新世界的開拓;歷史文化的熏習,則是人生必備的條件之一;至於對歷史變動與發展的理解,更是國民最可貴的能力。何況,王國維說得好,「只分楊朱嘆歧路,不應阮籍哭窮途」,因為「窮途回駕無非失,歧路亡羊信可吁」(《天寒》)。處身在新舊交沖、中西激蕩的偉大時代,加強歷史的認知,正是「窮途回駕」,時猶未晚,且也是避免「歧路亡羊」的唯一辦法。我們對此,自宜知所戮力。
只不過,中國歷史源遠流長,歷史文獻龐雜無儔,要瞭解中國歷史的源流與交遷,我們「必讀」的又該是些什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