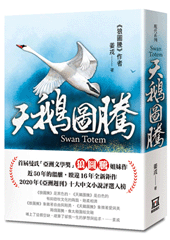
愛與美的極致與悲痛——姜戎談《天鵝圖騰》創作
我這個人平時很少與外界接觸,因為這三十多年來,我一直在構思和寫作兩部書,一部《狼圖騰》已出版十六年,另一部《天鵝圖騰》剛剛面世,所以一向不願意被瑣事應酬打擾,以保持我對蒙古大草原的新鮮純淨的感覺。
我先簡單地講一講寫這兩部書的意圖。我是一個有非常強烈的理想追求的人,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、民主,是我心底裡、骨子裡追求的目標。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太深厚了,深厚到什麼程度呢?從鴉片戰爭以後,凡是自由、民主、博愛這些現代價值觀及其成果,移植到華夏土壤上,種一棵死一棵,移一棵枯一棵。到了當代,最核心的東西基本上還是沒有活下來。這就是文化土壤的問題。
很多朋友曾經問我:你怎麼不再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了呢?為什麼去做「寓公」寫書?我回答說,這就好比在一片鹽鹼地裡種樹,那些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、民主的優質樹苗都活不成。近代以來,很多志士仁人都迫切地希望把那些偉大的樹苗移過來,卻一次次失敗,而且損失了犧牲了很多人。你遇到這種情況,是先改造土壤呢?還是先移栽樹苗?我早就認識和發現了這個問題,我覺得這麼幹是不行的,浪費了我們短暫的寶貴的生命。我當時就下了決心,首先必須改造文化土壤!
我的興趣比較廣泛,讀書非常多。從西方的世界來看,民主革命以後,推翻了封建帝制,然後復辟,再革命,再復辟……最後他們發現未經啟蒙、改造的文化土壤不行,於是繼續搞文藝復興,宗教改革,啟蒙運動。經過土壤改良後,理想社會的種子才能扎下根長成參天大樹。那麼改造土壤用什麼方式最好呢?主力軍是什麼?很顯然是文學藝術。假如我寫一篇有分量的理論文章,寫得再好,頂多幾百人上千人看,影響不了大部分人的觀念。只有文藝可以普及大眾直擊人心,而且我本來就是文學藝術愛好者,自幼學畫,小學時進西城區少年之家美術組,初中時進市少年宮美術組,高中時考進中央美術學附中,深受俄羅斯和西方美術和藝術的薰陶。還讀過大量的中外經典文學作品,在這方面有我的長處。文學可以成我的一個大事業,我願傾其所有之力去做。
我為什麼會寫《狼圖騰》和《天鵝圖騰》?因為我在草原當知青的時候,就想到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,後來研究歷史,又進一步發現:西方發達民族的祖先都是遊牧民族。原始白種人、雅利安人,都是遊牧民族。遊牧民族進入現代社會之前,經濟比較落後,但它有一個最基本的特點,沒在草原上生活過的人絕對認識不到:遊牧民族天性是自由的,自由是他們的靈魂,是他們生存的主要手段。自由是遊牧民族的本質,這是生產方式決定的。
而農耕文化則完全相反,它需要守土,你種了兩畝地,你不守土不耕耘出去遠遊,一回來那兩畝地已經變成了一片荒草,你還吃什麼?所以農耕民族的生存基礎就是守,守土。幾千年農耕文明守土的必然性,造成了中國人的保守習性。遊牧民族一遊就活,一守就死。我放過羊我知道,蒙古牧民一個月搬一次家,有的時候二十天搬一次,蒙古包周圍十幾里的草吃完了,牧民就要搬家。不搬家全家的牲畜都得餓死,人也沒法活。所以遊牧與資本具有共性:哪兒草場好,就到遊哪兒去;資本是哪兒好賺錢,就流向哪兒去。但別的部落也發現這個草場好怎麼辦呢?那就打,狼精神就上來了,善戰的草原狼就成了牧民的老師和崇拜的圖騰。資本也是這樣。所以我發現整個草原上有一種精神是值得漢人吸取和提倡的,這就是自由剛勇的狼精神,應該用這種精神來改良中國人的性格。尤其是中國從農耕為主的時代,進入現代商業、大工業和資訊產業時代。
我的另一個發現就是天鵝。天鵝的精神是什麼?我這部鵝書的腰封上有幾句話,就是「狼圖騰是黑色的,天鵝圖騰是白色的。狼圖騰象徵著自由與剛勇,天鵝圖騰象徵著愛與美」。我解釋一下:自由與剛勇,愛與美,一共包括了西方主要的三個神——自由神、愛神、美神,這三個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沒有的。中國有財神、灶神、門神等等,都非常「實用」,接中國人的「地氣」。
中國的婚戀觀是怎樣的呢?民間流行的是「嫁漢嫁漢,穿衣吃飯」。「人生一世,吃穿二字。」跟愛與美完全不搭界。所以愛和美作為觀念性的理想目標,在中國的價值觀裡是缺位的。中國的價值觀就是安穩地活著,沒有對於「自由」的嚮往。可是世界上如果沒有自由,就沒有自由創新精神所創造的現代世界,在中國也沒必要授予抗日戰爭英雄「獨立自由勳章」。而愛與美,和自由是同級別的神與價值觀,沒有愛與美,生活還有什麼意思。我們都希望追求美好生活,如果沒有美,哪有美好?沒有真正的愛與美,社會上的假惡醜必定氾濫成巨災。
所以,狼的自由與剛勇精神和天鵝的愛與美精神,恰恰是發達國家主要精神的核心。我當時就有一個雄心,想把這兩個精神,通過兩個圖騰把它表現出來。細心的讀者會發現,兩本書的最後都有一條:腹稿於一九七一年。其實狼與天鵝兩本書,幾乎是同時構思的,這兩本書像太極圖一樣,是一種遊牧文化的兩個方面,是剛柔相濟、相互作用的整體。但起初的構思,只有非常模糊的輪廓。《狼圖騰》為什麼寫得這麼難,因為我的對手是幾千年文化的深厚沉澱,傳統觀念難以撼動。所以我的書必須要寫得真實又真實、精彩又精彩、神奇又神奇。圖騰,就是至高無上的精神崇拜物,需要豐富紮實飽滿的故事內容,把它填充、支撐起來。
七十年末期到八十年代初,我在中國社科院讀研究生的時候,導師說你們寫書千萬別寫大題目,而要寫中題目、小題目,因為大題目你沒有幾大卷四五卷是寫不透的。可是我就選了「狼圖騰」這麼大的題目,寫起來要費很大的勁。幸好,我到了草原一開始就見到狼群,畏懼狼也喜歡狼,《狼圖騰》裡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我親歷的和直接採訪得來,掌握了很多很多狼故事。七十年代的草原還有很多狼群,那是真實的。好多我們同時插隊的知青都能證明。《狼圖騰》總算完成了,我把《狼圖騰》的大題目大系統填滿並支撐起來了。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人幾千年來對狼和狼精神的無知與偏見。
那麼《天鵝圖騰》呢,寫起來就非常麻煩和困難。寫這部書要比《狼圖騰》難十倍。為什麼?第一,在我們插隊的時候,天鵝崇拜在表面上幾乎已經看不到了,那時候,黃教、喇嘛教都被剷除了,更古老的敬拜天鵝圖騰的薩滿教,也早就蕩然無存。只有牧民愛天鵝,憎恨外來戶殺天鵝的感情,還有或鮮明或隱蔽的遺存。《狼圖騰》裡寫的天鵝,是插隊知青時代的天鵝故事,裡面包括外來戶大肆公開殺天鵝,吃天鵝的殘忍的事情。但要是把《天鵝圖騰》裡面的天鵝崇拜的故事,放到插隊知青時期的話,肯定不真實,也與《狼圖騰》基本精神不相配。
寫《天鵝圖騰》最難的第一個問題是時代問題,放在我草原下鄉的七十年代絕對不行。我插隊的時候,知青根本不知道有天鵝圖騰那個說法,即使有,也會被當作「四舊」毒草被打倒。那放在什麼時代呢?只能放在清朝的時候,因為清朝的時候,薩滿教還在,薩滿法師還在,天鵝崇拜、救天鵝養天鵝放天鵝的這種高貴的風尚還存在。《天鵝圖騰》時代背景必須放在滿清中後期,主要為了歷史的真實。
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確定以後,我要為這本書下的功夫,就是把草原最純淨、最純美的那種狀態呈現出來。我現在七十多歲,在草原的時候只有二十多歲,純淨草原的天鵝湖畔、天堂般的生活狀態始終保留在我心裡。
記得當年我就有意識地設法尋找六、七十歲的人,請他們講以前的故事、傳說、情節和細節,陸續搜集了那個時代的許許多多的天鵝故事,但還有好多天鵝的故事沒寫進去。比如說,我舉個例子,當年旅蒙商隊已有火槍,為了防馬匪。有兩個漢人拿著槍去打天鵝,那時,草原牧民敬拜天鵝,天鵝不怕人,經常飛得離人很近。其中有個老獵人「砰」地一槍打死了一隻天鵝,那天鵝落在岸邊水裡,旁邊小夥子剛要起身去撈獵物。老獵人按住他說,別動別動,那隻飛走的天鵝,准保會再回來的。果然過了一會兒,另一隻天鵝瘋了似地飛落到伴侶身旁,哀傷地叫著,想去救牠,但馬上又被火槍打死了。
這樣的故事我知道不少,你說能寫到《天鵝圖騰》裡面嗎?我覺得不能寫,因為太殘忍了,與《天鵝圖騰》唯美純淨的格調不符。但這個故事,證明天鵝伴侶確實是一生相愛相伴相守的。書裡女主人公薩日娜在一首的詩歌裡唱道:「天鵝的命是同愛同死的命,天鵝的愛是同跳同停的兩顆心臟」,是這樣,非常感人。有很多很多這樣的故事,所以我要躲開人群,保存心裡那種純淨草原的感覺。我生活在我的草原天堂,對那麼多天鵝故事進行篩選提煉,小說構思才慢慢成熟。
第二個問題。這也是我在《狼圖騰》寫完以後,過了那麼多年才完成《天鵝圖騰》的原因。蒙古草原的一大特色,就是蒙古人個個都是天生的歌手,喜歡用唱情歌來表達愛,如果你寫蒙古的愛與美,不寫情歌的話,等於迴避了草原愛情的主要表現形式。我很愛詩,但從來沒寫過詩,《狼圖騰》裡頭有一段民謠是我自己寫的。但在《天鵝圖騰》裡一下子寫那麼多詩,需要花費很多功夫。《天鵝》寫作中我前後寫了二十多首詩,最後選了十幾首詩。其中的天鵝詩有八首,而且都比較長,四段或五段,每段四行字、五行字、六行字的都有。我花了很多年時間研究詩歌,非常難。後來,漸漸找到詩歌的感覺,寫詩寫到動情之處,必然會有一種強烈的衝動。有的詩歌我在十幾分鐘之內就寫下來了。但也有幾首詩,反覆改了好幾年。現在書出版以後,各方讀者的回饋大多認為詩和故事情節結合得自然而緊密。詩歌的問題解決了以後,我才感到這部書具備了草原詩意的品質。
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很難的。現在愛情故事已經寫濫了,大家都不敢碰這個題目。怎麼才能把愛情寫得有新意,而且把自己想表達的對愛的理解寫出來,這特別難。後來我仔細研究,發現了一個秘密,今天在座的蒙古族作家興安可能知道,蒙古族牧民的愛情表達,跟漢族(尤其知識份子、小資)的愛情不一樣。蒙古族人的愛,不是說,而是唱、是做——做實事兒,一件一件一件做給你,他不說「我愛你,我愛你」,獻給你九十九朵玫瑰,一次獻,兩次獻,不是這樣,他是給自己愛的人,做許許多多的具體的事。
這本書裡男主人公巴格納向女主人公薩日娜示愛,總共只有一首詩,那也是最後逼得沒辦法才唱出來。他平時沒有語言表達,而是用一個一個行動表現自己的愛。大行動是做客棧,小行動是捕魚,炸魚、賣魚、不間斷地給薩日娜送魚糧菜的鵝食,送馬,撿蘑菇、搭建抗雪災的大棚等等一系列的事情。我寫愛情小說是蒙古人教給我的: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救你,先救下來再說,我得不到你的愛,但是我可以把你救下來,因為不救下她的話,她就會賣身為奴。
所以這個故事具有蒙古族的特點,你問興安是不是這樣?蒙古人不是口頭表達愛,而是用一件一件所做的事來表達。所以我就按照蒙古族表達愛的方式,把一件事一件事寫得非常細,所有做的事都是愛。巴格納就是為了一個目標,救下他愛的薩日娜,這種愛是可信的,真實的。感動我自己也打動讀者。我們知青當年在蒙古包裡,蒙古人非常善良,他們對知青的關心,就是一件事一件事幫你做好,不是說而是做。我再提醒一下,你們看的時候,要仔細體會那一件又一件的事,這樣也把蒙古原生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過程全看到了,就會身如其境,置身於純淨美麗的蒙古大草原,相信他們的愛就是這樣純粹、執著、濃烈而真實。
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不能展開講了。我認為這部《天鵝圖騰》,它的精神純度、文學詩意、以及對靈魂的觸擊度上,要超過《狼圖騰》。當然《天鵝圖騰》達不到《狼圖騰》那種緊張激烈的情節衝突、追求自由的精神價值的高度。但是在情感上,在藝術上,在美學上是超過狼書的。兩部書各有千秋,都是圖騰級別的。我是學美術的,最崇拜什麼?維納斯,愛與美之神。可惜中國沒有這個神。你在這本書裡能看到天鵝就是維納斯。我們需要自由神,我們也需要愛神與美神,有自由神、愛神、美神與我們同在,這樣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。
大家也許很想知道,我在寫作這兩部書的時候,是一種什麼狀態?我寫《狼圖騰》的過程中,經常有這種情況,忽然感覺到自己的靈魂不知道到哪兒去了,不是忘我,而是我不存在了,完全找不到自己了,靈魂飄飄上升,有一種宗教般的崇高感。寫到最後,我必須要把一塊幹的白毛巾放在桌旁,眼淚不是一滴一滴地滴,而是湧出來的。那種狀態就像神秘的網一樣,把那些虛誇、浮躁、華麗的詞彙都過濾掉了,筆下自然流出那些順暢的詞句。所以我認為寫小說,語詞的運用是第二位的,主要是要有那種寫作狀態和感覺。
這幾年我寫《天鵝圖騰》的時候,也同樣出現了那種宗教般的崇高的狀態。我的靈魂好像又有飄飄升天的感覺,自己找不到自己。寫到感情衝動的時候,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我有一位較我年輕許多的朋友,是個億萬富翁了,看鵝書的時候多次流淚,他每次看到流淚的地方,都要把那一頁用照片拍下來發給我,我發現打動他的都是詩。我覺得很奇怪,他流眼淚的地方,恰恰也是我流淚的地方,基本上是我倆同步共鳴的幾個點,也是藝術家最想達到的那種巔峰狀態。
在這部書裡,我還創新了一種方式:將天鵝與人混在一起、以人鵝不分的方式來寫愛與美、寫愛情、寫詩歌。使這部書進入一種「人間」難以到達的「天堂」境界。作家應該是靈魂的設計師和建築師,要打動讀者的靈魂,只有先打動自己的靈魂,才能夠創造出剛才陳明俊董事長說的「百年之書」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