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方的沒落(下)世界歷史的透視【書衣收藏版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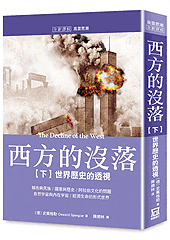
第十一章 始源與風景:自然宇宙與內在宇宙
你若看到黃昏的花朵,一朵接一朵,在夕陽落照之下垂闔著,你會感受到一種奇異的情緒,印烙在你的身上──一種面對著茫茫大地上,盲目而夢昧的存在,所感受到的謎樣的恐懼。無聲的森林、寂靜的田野、低矮的樹叢、樹上的枝椏,本身絕不動彈,只有風的吹拂,帶來一陣紛擾。而小小的蚊蚋,卻是自由的──它在黃昏的光線下,仍然自由舞動,愛去那裏,就去那裏。
一株植物,本身並不表示什麼。它形成「風景」的一部分,在這風景上,由於某一種的機緣,使它得以落地生根。而微曙、寒慄、每一朵花的垂闔──這些,既不是因,也不是果,既不危險,也不造成危險。它們只是單純的自然運行的過程,正在這植物的附近進行、陪隨這植物而進行、在這植物之中進行而已。個別的植物,是既不能自由觀望、也不能自由意志、更不能自由選擇的。
相反地,動物可以選擇。它已自一片沉寂的世界的「拘役」(servitude)之中,解脫出來。這一小群蜜蜂不斷在舞動,那隻孤獨的鳥仍然在黃昏中飛翔,狐狸偷偷潛近了鳥巢──這些,都是另一個大世界之中的,動物們自己的小小世界。水滴上的微生動物,小得人眼無法覺察到,它雖然只生存一秒鐘的時間,只以水滴的一角,作為生存的領域──可是,面對漠漠宇宙,它是自由的,是獨立的。巨大的橡樹,葉子可以懸掛多少的水滴,可是,它卻不能自由。
拘役與自由──在最終極和最深刻的分析中,即是我們藉以區分植物性生存、與動物性生存的差異所在。然而,只有植物才是全然而完整的存在,因為在動物的存有之中,含有一種二元對立的成分在內。植物,就只是植物,而動物,除了植物之外,還包括其他的性質。獸群聚集在一起,面對危險,恐懼戰慄;孩子哭泣不已,依戀於母親的懷抱中;人絕望地奮鬥,想要追求他的上帝,──所有這一切,都是想要從自由的生命,回歸到植物性的拘役中去,而他們本就是從這拘役之中解脫出來,而進入於孤單和寂寞的。
〔植物是屬於自然宇宙的(cosmic),動物則另有一項性質,它是與外在宇宙有關的一種內在宇宙(microcosm)。自然宇宙的一切事物,都帶有「週期性」(periodicity)的特色。它擁有生命的脈動節奏。而內在宇宙的一切事物,則具有一種「偶極性」(polarity)。偶極性固然表現在思想方面,但其實,所有的覺醒狀態,本性之中都帶有一種「張力」──例如主體與客體的對立、「我」與「你」的對立等都是。對自然宇宙的脈動節奏的感知,我們稱之為「感受」(feel);而對內在宇宙的張力的感知,則稱為「知覺」(perception)。德文中Sinnlichkeit─感覺能力、感覺性─一詞的曖昧性,實在攪混了生命的植物一面、與動物一面之間的差異性。事實上,前者永遠帶有週期的特性、脈動的節奏;而後者的特色是在張力,是在光線與被照體之間、認知與被認知物之間的偶極對立。
對我們而言,血液是生命的象徵。祖先的血液,流過了世世代代,把他們束縛在一個由命運、脈動、和時間所搭成的巨大連鎖之中。故而自然宇宙與內在宇宙,在此並皆浮現了出來。
「意識」一詞,頗為含混;它包括了「生命存有」(Being),也包括了「覺醒意識」(Waking-consciousness)。生命存有,具有脈動和導向;覺醒意識,則是張力和廣延。植物的生存之中,不具有「覺醒意識」這一要素。
對動物而言,與眼睛相對立的一極,就是「光線」(light)。生命的圖像,是透過光線世界,而捕攝入眼睛之中的。在人的覺醒意識之中,沒有任何事物,能擾及到眼睛的「支配地位」(lordship)。但一種不可見的上帝的概念,是人類超越性的最高表達,故而能超乎光線世界的界限之外。而在藝術之中,則只有音樂的方法,不必藉助於光線世界,故而能使我們脫離光線的統治。
即使在高級動物身上,「純粹的感覺」與「理解的感覺」之間,也自有其差別。語言的發展,使得理解自感覺之中,解脫了出來。脫離感覺之後的理解,便稱為「思想」。〕
在人的覺醒意識之中,理論性的思想之發展,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種新的衝突──「生命存有」與「覺醒意識」之間的衝突。這便使人類與動物,判然有別。動物的內在宇宙中,覺醒意識只是隸屬於生命存有的僕從,兩者自然結合起來,虎為一個活生生的單元,故而動物只是單純地「生活」著,而不會反省自己的生命。然而,一方面由於眼睛那無條件的統治地位,使得生命在光線之下,呈現為一種可見的整體生命;另一方面,當理解與語言互相結合時,卻又立即形成了思想的概念,與生命的反面概念(counter-concept),到了最後,實在的生命,便和可能的生命,發生了差別。於是,我們的生命不再是一往直前的,簡單明瞭的,我們有了「思想與行動」之間的對立。這在野獸身上,是根本不可能的事,可是在我們每一個人,已不但是可能,而且是事實,而最終,還要成為二者選一的抉擇。成熟人類整個的歷史,一切的現象,都是由此形成的。而且,文化所取的形式越高級,這一對立性,對於其意識存有的重要時刻的主導,也越完全。
〔人類的覺醒意識,包括了感覺和理解,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。於是,便遇到了知識論上的問題。覺醒意識,既兼容並蓄了相反的生命存有:而自其本身看來,則張力的世界,必然是嚴格和死板的,所謂「永恆的真理」,超乎所有的時間,表現為一種狀態;可是覺醒意識的實際世界,卻又充滿了變化。靜止與運動、持續與變異、已經生成的事物與生成變化的過程,這些對立,都指向於一種本質上「超乎一切理解」的事物,故而純從理解的觀點來看,必定帶有一種荒謬性。而如果求知的意志,在運動問題上歸於失敗,則很可能是因為:生命的目的,在這一點上,已經達致了。儘管如此,事實上,也正因為如此,運動問題一直繼續成為所有高級思想的重心所在。〕
運動的問題,立即而直接地,觸及到生命存在的秘密,它對覺醒意識是陌生疏離的,但卻冷酷地迫壓在覺醒意識之上。在研詰運動的問題時,我們強使我們的意志,去瞭解那不可瞭解的事物──「何時」、「為何」、命運、血液,一切我們的直覺過程所能觸及的深度。由於我們生來就有視覺,我們便努力想把這問題,置於我們眼前的「光線」中,俾使我們能實實在在掌握住它,而把它確認為具體的事象。
這是頗具決定性的事實,而運動問題的觀察者,並不曾意識到──他整個的努力,所追尋的目標,其實並不是生命,而是「看到」生命;也不是死亡,而是「看到」死亡。
我們不僅生活著,而且知道「生活」本身,是在光線之中,我們具體的存在的一種結果。但是獸類只知道生命,而不知死亡。如果我們是純粹的植物式存有,我們不會意識到死亡,而只是自然地死亡,因為在植物,感受死亡與死亡本身,是同一同事。而動物,縱使它們聽到死亡的呼聲、看到死亡的屍體、閒到腐爛的氣味,也仍只是眼看死亡,而一無瞭解。只有當理解,透過語言,而脫離了純粹視覺的知覺之後,死亡對於人而言,才成為他周遭光線世界中的,一項絕大奧秘。
惟其如此,生命才變成了誕生與死亡之間的,一段暫短的時間;而與死亡有關的另一偉大神秘──世代蕃衍(generation),也告產生了。惟其如此,動物對一切事物,所懷的混亂的恐懼,乃變成為人類對於死亡的確定的恐懼。由此,而造成了男女之愛、母子之愛、世代綿延、家庭、民族,而最後,世界歷史本身命運中,那無限深刻的事實與問題,也呈現了出來。死亡,是每一個誕生在光線之中的人,共同的命運;與死亡緊密糾合的,有「罪與罰」的觀念;有生存是一種贖罪過程的觀念;有超越這一光線世界,便能獲致新生的觀念;也有藉由宗教救贖,而能終止死亡恐懼的觀念。在對死亡的知識中,產生了一種文化的世界景觀,由於我們具有這種景觀,乃使我們成為人類,而有別於野獸。
第十二章 始源與風景:高級文化組群
〔人無論是為生命而生、抑或為思想而生,只要他正在行動或思考,他便是覺醒的,因而,也便即處身於他的光線世界,為他所調整的焦距之內。
在歷史世界的圖像中,知識只是一種補助之物:事象本身,呈現在我們所謂的「記憶」裏,好似沐浴在一種由我們生存的悸動,所掃掠而過在內在之光中。這在自然世界的圖像中,則表現為一種疏離虛幻、不斷展現的主題。縱使思想能規律自身,然而一旦思想變成了思想史,便不再能免於一切覺醒意識的基本狀況的影響。
每一時代,有其自己的歷史水平,真正歷史家的特點,就在於他能實現他的時代,所要求的歷史圖像。每一文化與每一時代,各有自己的認識歷史的途徑,世上沒有所謂歷史的本身。〕
即使是植物和動物的歷史,甚至地殼或星球的歷史,也不免含有寓言的成份(fable convenue),不過只是自我存有的內在傾向,反映到外在實際中的影象而已。研究動物世界或地層演化的學者,本身還是一個人,生活於其時代,具有自己的國籍和社會地位,所以,他不可能在處理事象時,消除一切主觀的視點,正如我們不可能,獲得一部有關法國大革命、或有關世界大戰的完全客觀的記載一樣。
我們所抱持的,有關地殼與生命的圖像,迄今為止,仍然處在自「啟蒙運動」以來,文明化的英國思想,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概念的主導之下──萊伊爾(Lyell)有關地質層疊形成的那種愚鈍的理論、達爾文的「物種原始」理論,實際上,只是英國本身歷史發展的導出物。他們摒棄了早期地質學家,凡布哈(Von Buch)與克威爾(Cuvir)所承認的,那些不可數計的災異和形變,而將一種依序而進的演化觀念,強置於極長的時期之上。並且,只承認科學上可計算的原因──實際上是機械性的「實用原因」(utility-cause)──才是演化的因素。
與十九世紀相較,二十世紀的重點工作,就是驅除此一膚淺的「因果系統」──它的根源,遠紹於巴鏤克時代的理性主義──而代之以一種純粹的「觀相系統」。在十九世紀,「演化」一詞,意指生命向其目的,不斷遞增其適應性的一種「進步」。可是,萊布尼玆出版於一六九一年的「原形」(Protogaea),一本充滿深刻思想的著作,即基於對哈茲銀礦的研究,而描繪出一幅世界早期的圖像輪廓,與歌德的圖像甚為相似;而在歌德本人,「演化」實意味著「形式」內涵的增加,以迄於「形式」的充分完成。故而歌德的「形式」完成,與達爾文的「演化」觀念,兩種概念恰成完全的對立,一如命運與因果的對立一樣。(這也正是德國思想與英國思想、德國歷史與英國歷史的不同。)
對達爾文主義,最終極的反駁,莫過於由「化石學」(palaeontology)所提供的證據。簡單的或然率,指出化石貯藏,只是一些試樣。而每一試樣,應代表一個不同的演化階段,故而我們應能發現一些僅屬「過渡時期」的類型,這些類型沒有確定的型態和種類。但是,並沒有此類的化石存在。我們只發現一些已歷經久遠時代,完全固定而不再改變的形式,一些不按「適應原則」以發展自身的形式。它們突然而立即地出現,成為確定的形態。其後,也並不趨向於較佳的「適應」,反而是越來越少,終至消失,然後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形式,湧現出來。在不斷增加的形式中,所開展出來的,是「生命存有」的各種繁富的種類和屬類。這些種類,自始存在,迄今仍存在,而並沒有過渡的類型。我們明白,在魚類之中,板鰓魚這一簡單形式,最先出現在歷史的前景之上,然後逐漸的衰絕;而由硬骨魚慢慢取而代之,成為最有勢力的純粹魚類型態。這也同樣見於植物世界中的羊齒植物和木賊植物,這兩者之中,只有後一種類,如今仍然存在於完全發展的有花植物界中。但是,對於這些現象,所作的「實用原因」、以及其他的可見原因的假設,並沒有實際的根據1。應該是「命運」,在世界之中,喚起了生命之為生命,喚起了植物與動物間不斷尖銳的對立、喚起了每一單獨的類型,每一「屬」(genus)、每一「種」(speies)。隨此一「存在」以俱來的,尚有一種專屬於形式的確定「能量」──經由這一「能量」,在「形式」完成的過程中,「形式」能保持純粹,或相反地,變成遲鈍與含混、或逃避地遁入無數的樣式中──而最終,成為此一「形式」的生命持續期,(除非有意外事件介入,削短這一持續),它總是自然地進入於此一種類的衰老時期,而最後終至於消失。
至於人類,一般對洪水時代的發現,越來越確切地指出:當時所存在的人類形式,即對應於現有的人類。毫無任何最輕微的演化特徵,可以表現出某一族類,確有實用主義者所謂的「適應」傾向。在地質學「第三紀」(Tertiary)時代的發現中,始終不曾尋到人類的蹤跡,這也越來越明晰的顯示:人類的生命形式,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樣,是起源於一種「突變」(mutation),它是「來自何處」?「如何形成」「為何如此」?始終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奧秘。事實上,如果確有英國人所謂的「演化」一詞,則既不可能有確定的地表層疊、也不可能有特定的動物類型,而只有一堆簡單的地質素材、和一團混沌的生命形式,這才是我們可以假定為「存在在掙扎」(struggle for existence)中,餘留下來的物象。但是,我們在周遭所見的一切,一直迫使我們相信:有一些深邃而突然的變化,發生於植物及動物的存有中,這些變化,是屬於「自然宇宙」的現象,絕不只限於地表之上。事實上,這即使不是超乎人類一切的觀點之外,至少也絕不是人類那囿限於因果的感覺或理解的視界,所能企及的。同樣地,我們也觀察到:迅捷而深刻的變化,自己出現在各大文化的歷史之中,沒有任何確定的原因、影響、或目的。哥德式與金字塔的風格,突然地呈現為完整的存有,正如秦始皇時代的中華帝國、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帝國一樣,也正如希臘主義、佛教、及伊斯蘭的出現,同樣地突然。每一個人,個體生命中的一些事件,其情形也與此完全相同;任何人若不能瞭解這一點,便絕不能瞭解成人、更不能瞭解孩子的生命。每一存有,無論其為活動的、抑或沉思的,都經由各個「時期」(epochs),而大步邁向於自我的完成,我們所須從事的工作,正是定出太陽系及恆星世界的歷史中的,這一些的「時期」。地球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、自由移動的動物之起源,就是這一些「時期」,故而,這是我們無法理解而只能接受的神秘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