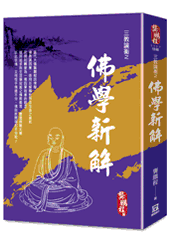
最近讀到台大哲學系教授楊惠南先生的新著《佛教思想發展史論》,頗有些感觸。楊先生是著名的佛學研究者,可是據他說,他原本卻是甚為排斥「佛學」,只注重「學佛」的人士:
我是一個講究「學佛」而輕視「佛學」的傳統佛教徒。我周遭的師父和老師,都告誡我:不要讀太多經典,因為那和解脫成佛無關。有一次,我請教過台中一位有名的淨土宗居士,問他在我讀完《阿彌陀經》之後,應該繼續讀些什麼經典?結果他反問我一句:「讀那麼多經典幹什麼?」還有另外一位法師也叮嚀我:除了《阿彌陀經》《楞嚴經》之外,不許再讀其他的經典!當時,我是多麼相信這些老師和師父的話,我忘了每天早課時,在佛菩薩面前所發下的弘願:「法門無量誓願學!」事實上,就一個剛剛進入佛門的我來說,並不瞭解這句弘願的真義。原來,在佛門中,強調「學佛」的人,常常批評那些研究「佛學」的人士只是「說食數飽」、「畫餅充饑」,永遠不能解脫成佛。現在突然要我放棄「學佛」的修行,跳入自以為矛盾衝突的「佛學」異域,著實困擾了好一陣子!
楊先生後來是抱持著悲痛壯烈的心情去進行佛學研究的。這一段佛學與學佛的矛盾衝突,現在當然不會再困擾他了。但是整個佛教界呢?不是還一樣存在著佛學與學佛的矛盾嗎?佛教界不仍是只重學佛而較忽視乃至貶抑佛學嗎?
我在《國際佛學研究年刊》第二期的序文中,曾經談到當前佛教界所必須面對的問題,其中之一便是「教義的研修」:
台灣佛教的活動固然十分蓬勃,家家阿彌陀、戶戶觀世音,各寺廟無不香火鼎盛,經懺法會亦從不間斷。每逢法師開示或宣講,輒見萬頭攢動,即使是達官顯宦,也往往參禪打七。但在這類佛教活動極其繁盛的背後,卻是對教義的極度陌生,表面熱鬧而內裡空洞。因為絕少人瞭解什麼佛教的教史與教義,他們信佛拜佛,僅是隨俗或祈求功利福報而已。某些以學佛修密為時髦的知識份子,亦以神秘經驗為主,談佛法義理,類皆荒誕不經。這是佛法傳佈的危機,我們不能只要求信教者做功德而不讓他們明白自己信的究竟是什麼。宗教的道理,關涉了客觀真理及個人終極關懷兩個方面,此為何等大事,而可以迷糊蒙混乎?故如何加強信眾對教義之瞭解,如何在教義的研修方面提出我們這個年代的貢獻,實在是個大問題。從歷史上看佛教的發展,每個時代都有其對教義的闡發,我們這個時代可不能繳了白卷。
信教而不知義理,蔚為風氣,成為當今佛教的大問題,相信此處說得並不過分。這不是教界及信眾僅重學佛修證而不重佛學使然嗎?
正因佛教界不甚重視佛學,故一旦蓋寺廟,各方捐獻極多,若是辦佛學院或研究中心,信徒、寺院都興趣寥寥。僅有的幾座佛學院,也往往經費困窘,發展困難,使得佛教教育迄今仍未步入正軌,整個佛教界仍然缺乏夠水準的弘法人才,對於信徒們所提出的各種問題,例如經典的義理、歷史發展所造成的教義變化、各宗派教理的差異、不同區域教理的分別及其發展狀況等等,往往不能正確或深入地解答。因此,我們會發現,目前的佛教界似乎是一知半解、糊裡糊塗的弘法人員,在指導著茫無頭緒的信眾。盲以導盲的情況,實在令人憂慮。
或許一般信仰佛教者並不以為這是個問題,只要佛教的道場仍然興旺、法會仍然盛行、其所推動之宗教慈善事業仍為社會所肯定,佛教彷彿就會一直蓬勃發展下去。這真是大謬不然之見。
須知中國佛教自隋唐以來,一般都認為宋元明清已漸衰頹,晚清以來始漸復興。而宋元明清諸朝民間信仰佛教者難道少了嗎?道場、法會、經懺又何嘗不興旺呢?佛教所辦的養老、慈幼、救濟、租賃事業不也十分普遍嗎?既如此,何以謂其為衰?於此便可見教義發展之重要了。隋唐以後,佛教的教義已無太大發展,流行於民間之佛教信仰,事實上僅成為一種缺少靈魂的儀式化行為,燒香、拜佛、念經、吃素以及超度亡魂而已。整個佛教,在個人,便是欲求往生淨土或利益福報(求菩薩佛祖保佑平安富貴、子孫昌旺之類);在教團,則是趕經懺辦法會(甚至出現迎財神之類法會)。
這種儀式化的結果,自然就形成了佛教的世俗化與庸俗化。拜佛祖菩薩的人,視佛祖菩薩其實與大樹公石頭公無異,求其保佑、豔其靈異罷了。此豈仍可稱之為佛教耶?佛教講因果,係用以解釋世界及生命之緣起,民間則轉變成為一種「善有善報,惡有惡報,因果報應,相與循環」的觀念。這與追求無生涅槃寂滅之佛教義理,實是南轅而北轍。以此信佛,又何怪乎佛道不分、佛與民間雜祀不分呢?換言之,儀式化、庸俗化之後,佛教更可能面臨「異化」的危機,變成佛教的對立物,導致佛教死亡。
宋元明清佛教界之發展正是如此,所以才有晚清佛學的復興運動。從楊仁山居士設金陵刻經處刻經開始,重新教人重視經典、讀經、注釋詮解經典,一步步走向教義的探索,從而找回佛教的真精神,把佛教發揚起來。因此,我們可以說,佛教之衰,即衰於其道場莊嚴、法會盛大、經懺流行、慈濟事業興旺;而其復興,則是經由佛學之研究才使其復興的。
歷史的教訓,豈能漠視?現今佛教之所以社會形象較以往好些,不再被視為庸俗迷信,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教界努力做社會工作(例如「淨化人心」活動)及社會福利(如慈善、醫療、救助)等等。但這不是佛教界才能做或才會做的事。任何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團體、任何宗教團體也都能從事於茲。何況,只要政府在社工社福業務上更能盡其職責,此類工作即能充分被替代。故佛教界不能以善為社工社福事自矜,更不能自我定位於此。且救貧濟眾,若徒救其貧、恤其病,而不能令其法喜充滿,又怎能自稱是佛教事業?然則,欲令病者得法,我們自己對法的理解如何?得法了嗎?本身對佛法不瞭解、也不注意,又怎能施法濟世,普度眾生?
宗教與一般社會團體不同。它並非為解決人之社會生活困難而存在,乃是基於解決生命價值意義之終極問題而存在的。因此,世俗化或庸俗化的走向,縱或因其具有政治社會功能而風光一時,其利未必便能溥久,對知識分子也不會有吸引力。這些決定社會價值觀和思想發展趨向的知識階層,倘不能被佛教所吸引,勢必尋求其他代替的宗教,這對佛教是相當不利的。即或知識份子不改選其他宗教,仍企圖從佛教中獲取其安身立命之契機,他們也常會因為反世俗化而走向神秘化,不重視宗教的社會工作福利事業,而著重個人修持體證的宗教感應驗印。這時,如若缺乏佛學的導引,便極易流於異端神秘經驗,大講神通靈異。這種發展,事實上已成為台灣佛教界的隱憂,許多新興教派拓展均極為迅速,所談雜於風水星相嬰靈神通之間。此皆因佛教之正知正見正聞正信不彰,信佛者不得其法使然。長此以往,佛教焉能不日益異化?
當然我不是說佛教發展上的一切問題都導因於佛學研究不昌。佛學不受重視只是現今佛教發展的問題之一,但由於佛教界普遍重視學佛而不看重佛學,致使佛教日漸儀式化、世俗化、庸俗化、神秘化,產生了異化的危機,則是非常明顯的。我們必須注意這種趨向。
(二)
但這也不是隨意呼籲幾句「重視佛學」,或歸咎現今佛教界人士不明事理便能解決問題的。佛學與學佛的衝突或緊張關係,其實有理論上的深刻原因。唯有正視這一事實,方能逐漸疏理兩者之關係,使其各安其位或彼此互益。
為何說學佛與佛學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其深刻的理論原因呢?
因為人類面臨的知識,基本上有兩類,一種是可以客觀認知、判斷的,如數學上的定理定律,如地球繞行太陽,如憲法及諸制度,如歷史事實楚漢相爭而項羽自刎於烏江之類,是可觀解、可形成理論、可客觀討論的知識。
另一種知識則涉及人的「存在態度」。該知識是否有價值、有意義,須是主體才能決斷、才能肯定、才能有態度的。所以這種知識只能在具體存在的個人身上說,客觀的知識要轉成主觀的才有意義。佛經上說「如人飲水,冷暖自知」者,即指此種知識而言。人對於不安、失望、痛苦、怖慄、放棄的理解,均屬於這種知識。無此類感知者,這些詞句對他便無意義,正如不信基督教的人,「神愛世人」、「基督以其寶血洗淨我們的罪」、「諾亞方舟」、「死後審判」等,都是不知所云之空洞言詞,對他毫無意義一樣。
相對於前述那種可觀解的知識,這種知識型態可稱為「實踐的知識」。這種知識不是說客觀上我覺得有佛陀、知道佛陀的教誨即是三法印十二因緣,而是只有我們在實踐性地學習佛陀之教法時,才能真正理解什麼是佛法。猶如唯有親自去飲水,方能知其甘澀與冷暖。
從這個意義說,一切宗教,基本上都是實踐性的知識,若僅從理論上去觀解之,而未進行工夫實踐,確實是難以進入宗教之核心的。學佛人士著重於踐履工夫而反對客觀的理論的佛學,基本上並無錯誤。
然而,縱使承認了這一點,我們仍然會發現:宗教在發展流布的過程中都必須要「傳教」。對於尚未信仰(亦即在存在之態度上尚未肯定此類知識,也對此類知識尚未進行實踐性認識)其宗教的群眾,這些已飲水者,勢必要將其主觀實踐所得之知識客觀化,轉換成為可觀解的理論性說明,否則旁人如何能夠瞭解?這一情勢,保證了主觀實踐性知識必然有轉換為客觀理論性知識的可能。人們正是基於這種可能,才能衡量甲宗教與乙宗教之間的高下是非,來重新決定自己的存在態度:或仍堅持原有之信仰,或轉而接納新的宗教。同樣地,這一情勢也說明了,在宗教中事實上存在著大量可觀解、可說明的理論性知識,否則該宗教便無法向外人說明其教義,無法傳佈。
宗教中並存著實踐知識與理論性知識這個事實,往往造成了宗教內部的困惑。究竟在宗教裡,該以信仰(實踐性知識)為主,還是可以以知識(理論性知識)為主呢?
這個問題,其實不僅在宗教中有,一切所謂「生命的學問」中也都有。如儒家之學,本質上即是種實踐性知識,強調成己成德,踐履躬行。但儒學內部卻也有「漢學」、「宋學」兩大體系的衝突。宋學對於儒學的性質,偏重在修養面,主張克己去私,修身養性,窮理盡性;漢學則注重經典,講究客觀的理論性知識,因此要博學、考訂篇籍真偽、訓詁文字、辨析名物制度。在宋學之中,又有程朱與陸王的不同。以漢學、宋學來分,漢學代表「道問學」的傳統,宋學代表「尊德性」的傳統;以宋學內部來說,程朱又可稱為宋學中的「道問學」,陸王則為宋明學中的「尊德性」一派。講陸王學的人,認為走漢學一路者完全不能觸及儒家生命之學的精神血脈,都是外在的知識堆積而已。講漢學的人,則批評走陸王心學一路者根本引用了偽書,文字解讀也不正確,對於孔孟諸子發言時之歷史情境更缺乏瞭解,任意自由心證,講什麼道統心法,根本就是胡扯。雙方互諍,迄今未已。
類似儒學的爭論,也存在於佛教中。學佛者強調「行」,類似儒家之所謂尊德性;言佛學者強調「知」,猶如儒者中之講道問學。二系分流,一偏行入,一偏理入。行入者證福,理入者見慧。行入者悲,理入者智。行入者重行,理入者重解。故「學佛——信——行入——福——悲——行」、「佛學——知——理入——慧——智——解」恰成一相對之結構,彷彿儒學中有漢學與宋學、尊德性與道問學之分那樣。
這樣的對比,還可以繼續深化下去。例如藍吉富先生即曾將佛教分成「知識份子的佛教」和「非知識份子的佛教」。這便不是說佛教中有理入與行入之分,而是說佛教中有一種是無論行解都較單純的宗派,這些宗派,整體來說較偏於行門,其理論亦甚簡約,易於持循。此即可稱為非知識份子的佛教,如淨、密、禪等,重修持,理論均甚簡捷。相對來看,像三論、唯識、天台、華嚴諸宗便可說是較具系統,理論複雜,重視經論法度,因此較有學術性價值,可稱為知識份子的佛教。當然天台等宗亦有修持法門,如天台有「止觀」之類。但其理論性格較強,由《小止觀》、《法界次第初門》、《釋禪波羅蜜》、《摩訶止觀》等書構成一套詳密完備的修持體系,對修持中之次第與可能發生的病患、魔事、境界、對治方法等,均有詳密的討論,顯然較禪宗之頓法要客觀化、理論化多了(見藍氏《二十世紀中日佛教》所收《現代知識份子佛教信仰》一文)。
即就禪法而論,印順導師也提到兩種修禪定的方法。他認為《雜阿含經》與《中阿含經》對於禪定的講法有精神之不同;《雜阿含》重在慧的體悟,
《中阿含》則較重視四禪、八定、九定的說明。故後來大乘經典中繼承《雜阿含》定慧綜合的風格;小乘薩婆多部卻分別定慧,專在四禪八定上去分析。又如一切有系,偏於由定中觀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、無常、無我而證慧解脫,但定本身不是慧,定境也不是解脫;大眾分別說系,則謂滅定亦即煩惱滅,定可以是空理之定,所以定與慧是合一的。(見《性空學探源》第三節)這兩種區分,事實上也就是一種偏於慧,一偏於定。
另外,韋伯在《宗教社會學》中則主張早期基督教、古伊斯蘭教、古猶太教都是「反理智主義之宗教」,其經典與信仰內容,僅為一些宇宙起源之說詞、預言、歷史、律法、聖誡,此外並無太多特定的理智觀點。換言之,這些宗教的核心,在於信仰。但亞洲各大宗教之教義卻多為知識份子所創,此即理智主義者之宗教。此類宗教,多反對精靈、自然、鬼神崇拜,反對大眾化巫術。它們由知識份子擔任其主要傳播者,甚至宗教也成為知識傳統的主要來源,成為哲學知識的形式。他舉佛教為例,說:「佛教和耆那教(Jainism)的拯救教義及其他與此相關的教義,都是靠知識子中的那些經過吠陀(Vedas)訓練之菁英傳播。」(見其書第八章)
以上這些看法,均顯示宗教會在處理信與知之問題時,因其不同而區分成兩種類型。與古基督教相比,佛教不講啟示(神或上帝顯現其自己,稱為啟示),也不講人對啟示有所反應的信仰。佛陀乃是以其對人生世界之理的覺悟而講緣起。此乃其對世界與人生之理論性解釋,故基本上是透過思維辨析而得,非修持、感應、神啟而獲。這就有知識份子理智主義的色彩。但在佛教內部,因為佛教畢竟是一種宗教,不純是一套哲學,因此,思想落入存在的實踐層,究竟該如何去印證、去獲知佛陀所說之理,仍然構成一實質之問題。由於對此問題處理方法之不同,佛教內又可再分成知識份子的佛教和非知識份子的佛教等等。
或者,在宗教流傳擴大的過程中,也必然使得知識份子宗教本身產生分化。韋伯言道:「只要一個宗教變成了一種大眾宗教,那麼,由知識份子創立的救贖教義及其倫理的發展,往往會出現某種秘教或某一貴族階級的倫理道德要求,以滿足受過教育之知識份子的需求;而此同時,該宗教又會逐漸變成某種大眾化且具有魔力的救世主宗教,以便滿足非知識階層人們之需要。」換言之,宗教雖或為知識份子所創,然既成為大眾宗教,便可能出現屬於社會大眾的神聖化、禮儀化、世俗化、民間信仰化傾向,以及反抗此一傾向的知識份子們所發展之內在化、理論化、出世化傾向。
此一分化狀況,倒過來說也是一樣的。非知識份子所創的宗教,雖重於實證而輕視理論知識,或偏於信仰而不願費力去從理論上證明與說明其信仰之理據,卻也可能在傳播擴大後發生分化或質變。例如禪宗,本是強調「不立文字」的,惠能更是根本不識字。其理論重在直指見性,簡易斬截,自當屬於非知識階層之宗教類型,故唐宋以後,流傳於民間甚盛。然而,此宗之簡易,對知識份子乃竟有另一種吸引力,因為具有一切理論知識之後的渾化境界,與完全無理論知識的素樸境界是有其類似性的。因此文士哲人亦酷喜談禪。禪之簡易直截,乃竟轉而成為超絕言象的智慧高峰,只有冰雪聰明者才能攀躋,以致機鋒如同啞謎,公案成為懸案,茫無頭緒,莫測高深。近人呂澄批評禪宗:「重智輕悲,偏於接引上機,和平民的關係比較疏遠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另一個例子,則是基督教在中古時期的發展。早期基督教係以信仰為主,乃希伯來文化之一支。其後傳播日廣,與希臘羅馬文化接觸融合後,希臘哲學傳統便在鞏固基督教信仰之理論面,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援。以至整個中古基督教神學均由經院、教團所掌握,成為知識份子型態的宗教。
由此看來,宗教的理論知識性與其宗教修證信仰行為之間,實存在著極為複雜的動態關係,它們之間的激蕩與衝突,可能就顯示了宗教發展的軌跡。
(三)
從佛教的理想來說,悲、智、願、行,應該是合一的,《佛說阿彌陀經》謂阿彌陀佛曾發四十八願,其中便包含「修行無礙」和「說法順智,誦經演說,無邊辯才」。可見行入與理入俱臻者方能廣修福慧。但佛菩薩中也有只修行不修智的,例如觀世音便是。《華嚴經入法界品》曾云觀音告善才童子:「我修大悲法門,願救護一切眾生」,因此他也是最受民間尊崇信仰的對象,與那些「重智輕悲」的菩薩不同。然從整個佛教看,此畢竟只是方便,所以觀音只能成為阿彌陀的輔佐之一,另一位輔佐則是大勢至菩薩。大勢至菩薩是相對於觀音之悲而顯其智,其智慧之光,能使大眾離三塗苦,其無上力能給予眾生菩提心種子。依經文所述,阿彌陀佛與觀音、大勢至三聖乃是相繼補位成佛的。可見佛教甚為明白:在佛法傳播過程中往往是悲智遞運的,但其歸趣,畢竟應以悲智合和為宗旨。此西方三聖之象徵意蘊也。
除了大勢至菩薩外,佛教中尚有一位智者之象徵,即文殊菩薩。所謂文殊慧劍,寓悲於智,「為佛道中父母,譬如世界小兒有父母」(《放缽經》),暗示了一切諸佛皆須智慧乃能成就。與他相對的,則為普賢。猶如大勢至與觀世音,善才童子訪求五十三位善知識,從文殊始而於普賢終,正象徵醒覺於智慧而終於願行,智與行也是不可偏廢的。在華嚴三聖的關係中,毗盧遮那佛,左普賢右文殊,即為大行大智合而成佛之意。
同理,釋迦牟尼佛左為苦行第一的大迦葉尊者,右為多聞第一的阿難。行解合一,乃得果行圓滿。意蘊與西方三聖、華嚴三聖完全相同。
這些象徵語言,都告訴了我們:佛教是真正理解到宗教生活中行解有衝突或分立現象的宗教,故強調悲智雙運、行解合一、福慧雙修。但行解既有衝突,如何雙修合一呢?從文殊的例子看,似乎佛教基本上走的是一條「以知成信」的路子。也就是說,佛教並非自然崇拜、鬼神信仰或精靈奉祭之類宗教,它不講究神跡感應與啟示,乃是以信仰佛陀對人生與世界之證悟為內容,以學習佛陀思想與人格為目標。信徒要在人格及思想上成為佛陀的追隨者,必須對佛陀的人生證悟有所理解。無此理解,不明白緣起的道理,如何修證?此所以是以智成信。
由此入者,方為正途。若不重空理,遽修證,恐怕並非上策。印順導師曾批評許多偏好禪,急求證入的人,落入了「沉空滯寂」之境,認為只有強調空的「重知見、重慧學,可以給這般重定者一種改變」。又說現觀有兩種,一種是親切明白且直接的體驗,乃直覺之經驗,非意識的分別或抽象的說明。
此類神秘經驗,為各宗教所共有,修持者親行實證的即是此種體驗。但許多宗教信徒們是以此種經驗為其理想境界的。他們以狂熱的信心,加上誠懇的宗教行為,或祭祀、或懺悔、或禁食、或修定,由精神的集中,迫發出一種特殊的經驗,在直覺中或見神或見鬼或見上帝,有種種神秘的現象。佛教之現觀則不同於此,認為學佛而專注重在此種直覺上,每易與外道相混,失卻佛法的特質,不免走上歧途。因為此種現觀直覺並未通過理智,故易混入由信仰及意志集中而生之幻象,雖確有內在之體驗,卻與真相不符。
佛法之現觀,號稱正覺,就是因為它特重理智,是通過理智之思擇。由多聞、尋思、伺察、簡擇種種程序,獲得正確之觀念後,再以誠信、集中意志去觀察審諦,以達到現觀。所以是如《阿含經》所云,「先得法住智,後得涅槃智」,從聞而思、從思而修、從修而證(見《性空學探源》,第十六、廿六頁)。
印老所指出的,適與我所主張佛教應「以智成信」之途徑相同。蓋佛教徒修習佛法本應如是。凡僅求修定,侈言體驗境界,而於佛學蒙焉囫圇者,恐怕多屬狂花客慧,幻象妄見而已。
因為以智成信,對教義以及自己為何修?修什麼?方能有較準確的理解,較不會越修越偏離佛法,或在不甚切要處斤斤計較,卻在大綱維、大關鍵處滑移流宕。
例如許多學佛者將「茹素」視為是否虔誠學佛的重大關鍵,不戒葷腥彷彿便失去了學佛的資格,甚或將吃素神聖化、本質化,謂殺生不戒葷者是造了殺孽、會下地獄受苦、會輪迴入畜牲道去受報應……
事實上,佛教的教理中,殺不殺生並非根本義,佛弟子之戒律生活中或茹素、或不戒葷腥,亦無一定之規定,何必執著於此呢?佛教徒在西藏、蒙古、西域,都習慣吃肉,因蒙藏人習俗不吃青菜,只用茶去除油膩而已,此等地區,焉能以不殺生、吃素來要求?佛教由西域傳進中國,原來也是葷腥不甚禁的,直到梁武帝頒佈《斷酒肉文》,提倡斷酒肉之後,中國佛教徒一般才不食肉。因此,吃不吃肉,與佛教的思想主旨及倫理要求,基本上不甚相干。雖然我們也可以從佛經中找到護生戒殺吃素的一些文字佐證,但我懷疑護生戒殺吃齋這些,多是受道教「貴生」思想的影響使然。提倡這些,並未觸及真正的佛法的核心;強調戒律生活應以此為主要內容,也是對佛教精神的理解偏差。若有人以齋戒表示誠信以及對自己意志身心的鍛煉,當然很好,但在此不甚緊要處執固不肯放鬆,就無謂得很了。
佛經中還有許多跡近邪魔的東西,例如《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審惡宿曜經》,乃唐三藏沙門不空譯,類似今日之黃曆,說明日月星象的位置變化,以及人應如何應對。可是它並不只教人趨吉避凶,更要人隨宿曜之吉凶善惡而為善為惡,如云:「胃星張箕室。此五是猛惡宿,宜守路險行劫行盜,構鬥端起設誑,博戲攎捕,強梁侵奪,奸非淫穢,圖城斫營,造械具戰具,書兵謀,放毒藥,施殘害一切艱難事務,悉須為之。」這是教人去打劫行搶、姦淫侵奪了。此非大有邪氣乎?
又如《文殊師利耶曼德迦咒法》教人於黑月十四日取屍陀林木燃火,取赤芥子和血及毒藥等,咒燒成灰。將這灰撒在人身上,人就陽痿了,婦女也不能和丈夫行事。若強欲性交,男子陽具會壞爛,女人陰門會出蛆。諸如此類講術法、神通、咒力的經典非常多,其術法亦千奇百怪,如《曼殊室利焰曼德迦萬愛秘術如意法》、《穢跡金剛百變法》、《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將佛陀羅尼經》、《龍樹五明論》、《青色大金剛藥叉辟鬼魔法》等,不勝枚舉。這些經典,或教人畫符,以朱書此符吞之滿七日即有種種妙寶自然而至,若求他財物,當「書彼人姓名於符下,其人立即送物到」;或教人隱身術;或教人念咒,因為要「男人上年欲求官進職,貴人見之歡喜愛念」。凡此種種,載入《大藏經》中,誰也不能說那不是佛法,但學佛者是不是就要學這些?
在此等處,便見得佛學的重要了。唯有瞭解佛教的基本義理,明白它的發展、流布、演變過程,方能有所檢擇、有所判斷,所信所修才是正信正修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