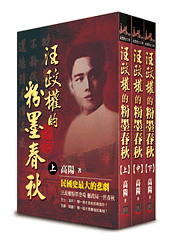
「丁默?原來是中統的高級人員,居然認賊作父,太不可原諒了!所以一定要制裁他。以他在敵偽政府的身分,以及他反叛組織的重大罪行,如果能夠消滅了他,是件太有意義,對國家太有貢獻的事。立德、立言、立功三不朽,蘋如,妳建了這件大功,在歷史上就佔了一席之地了。這是人生難得的際遇,妳不可錯過。」
鄭蘋如是外向的性格,覺得冒這個險很值得,也很刺激,心裡已經動了;但是,她在感情上不能不作顧慮,因而沉吟未答。
陳寶驊當然也想得很周到,看她的臉色,知她的心事,當即又說:「至於妳我的感情,絕對不受這件事的影響。是我向妳提出的要求,妳就算為我犧牲,我永遠都會感激妳、尊敬妳。」
有此保證,鄭蘋如再無顧慮,慨然一諾,照陳寶驊的設計去進行。先是找個藉口請丁默?幫忙,然後為了酬謝,請丁默?吃飯,陪他跳舞。就這樣,很快地讓丁默?迷住了。
「你們要動手,就趕快動手。」鄭蘋如對陳寶驊說:「機會隨時都有,早點把事情辦完了,大家輕鬆。」
「是的,是的!我們在積極籌劃,快了,快了!」
他是有說不出的苦。原來中統的工作重點在搜集情報,行動方面幾於無拳無勇。向軍統去借將當然也可以,但獨得的功勞讓人分去一半,卻又不甘,苦思焦慮,並無善策,就只有找助手來商量。
他的親信助手有兩個,一個是他的至親,名叫嵇希宗,還有一個是專員周啟範。
陳寶驊說:「這個行動最難的部分是,能夠左右丁默?,既然鄭蘋如叫他往東,他不敢往西,可說最難的部分已經完成了。至於下手,不過是一舉手之勞,只要有人,不是難事。」
就是沒有人!嵇希宗跟周啟範面面相覷,心裡的想法相同。
「重賞之下,必有勇夫。」陳寶驊說:「我們花錢去找個人來。」
「啟範,」嵇希宗說:「你是恆社的,總有路子吧?」
「路子怎麼沒有?不過要找靠得住的,不是三兩天的事。」
「一個星期。」陳寶驊問:「如何?」
周啟範想了一下,點點頭答應下來;問一句:「找幾個?」
找幾個要看行動計劃,於是丟開人的問題,先研究如何下手?當時決定了兩個原則:第一、不能在丁默?及七十六號的勢力範圍之內;第二、要在鬧區馬路上。這兩個原則,都是為了行動得手以後,易於撤退,不然,後果會很嚴重,而且也不容易找到人。
「照此原則,人少了不行;不過也不必多,以四個為最適當。」陳寶驊對周啟範說:「人歸你找,槍歸我借。」
這又遇到難題了。槍不難借,難在攜帶,英、法兩界動輒「抄靶子」,攜槍在身被抄到了,全盤計劃立刻打翻,所以手槍不宜預先發給行動人員。比較妥當的辦法是,行動之前半小時或一小時,在現場附近覓一處地方集合,臨時發槍,立即行動;事後回到原處,交槍解散。
等聽取了鄭蘋如的意見以後,細部的計劃擬出來了。時已入冬,設計由鄭蘋如向丁默?「開條斧」,為她買一件灰背大衣。上海最大的皮貨店,是靜安寺路同孚路口的「西伯利亞皮貨公司」,但不必預先說明要在哪裡買,免得丁默?起戒心。反正到時候隨機應變,終歸引誘他到那裡就是。
不但要引誘他到那裡,而且方向應該自西往東,因為西伯利亞皮貨公司坐南朝北,汽車靠左行駛,就只能停在對面,丁默?來回穿過馬路,才有下手的機會。四個人分兩面,兩個看住他的汽車,兩個守在皮貨公司門口,丁默?就怎麼樣也逃不掉了。
人找到了,槍也找到了,集合的地點比較難找,但終於亦能解決,是借了卡德路有名的浴室「卡德池」斜對面一家診所。只是四支手槍要由南市運到公共租界,卻不能不慎重。「抄靶子」是越來越厲害了,在租界上,隨時隨地都可以被攔住檢查,怎麼辦呢?
陳寶驊想到他一位叔叔,當初從上海運槍械,送學生到黃埔去的往事,設計出一個辦法,找一個有襁褓之子的媽媽擔任運槍的任務。
所謂「襁褓」,是八仙桌面這麼大的一方薄棉被,將嬰兒對角放在上面,先摺下面,再摺左右,全身包裹,只露出一個小腦袋。南貨店買蠟燭也是這種包法,所以俗稱襁褓為「蠟燭包」。
抄靶子不會抄「蠟燭包」,四支手槍藏在那裡面,萬無一失。但有兩個先決條件,第一、媽媽的膽要大;其次,四支手槍塞在「蠟燭包」裡,狼狼犺犺,嬰兒不會覺得舒服;不舒服要哭要鬧,也是麻煩,所以要找一個耐性很好,不哭不鬧的嬰兒。
這也很難,因為誰聽到這種事都會害怕,而且太太們總比較愛說話,小菜場中遇到,閒聊家常,無意中洩漏出去,大禍立至,所以只能通知同志,暗底下分頭物色。
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,終於找到了一位張太太,三十出頭,頗有鬚眉氣慨;一個八個月大的男孩,生來極乖,種種條件,並皆適合,陳寶驊開口一說,張太太慨然許諾。
「太好了!」陳寶驊很高興地說:「張太太,我送妳一千塊錢,小意思。」
「不要不要!」張太太雙手亂搖,「為國家嘛!能夠做好這件事,將來說起來,我也很有面子。」
陳寶驊以為她假客氣,等將鈔票掏出來,不道張太太要翻臉了。
「陳先生,你也太小看我了,這是性命交關的事,莫非你當我這條命只值一千塊錢?」
「是,是!」陳寶驊改容相謝,「我錯了。」
辭出張家,陳寶驊即去訪周啟範,道是「萬事齊備」,連「東風」都不欠,只待詐降的「黃蓋」將「曹操」勾引了來送死。
「槍呢?」周啟範問:「是不是先運了來,藏在集合的地方,要用就有,比較方便。」
「這不行!我想過。」陳寶驊說:「那家診所人很雜,萬一露了眼,反倒不好。這位張太太辦事相信得過,到臨時再運好了。」
於是通知鄭蘋如,可以「開條斧」了。那時丁默?迷她迷得神魂顛倒,只要她開口,說什麼就是什麼,當時便要出門上皮貨店,反倒是鄭蘋如不願。「我跟你說著玩的。」她說:「我又不是沒有皮大衣,何必這麼急?」
她這樣故作大方,是因為要騰出工夫來,好讓陳寶驊準備;同時也要等一個便於下手的適當機會。當然,這種機會並不難找。
「後天中午,滬西有個朋友請他吃飯,他那個朋友,我也認識,所以他邀我一起去。」鄭蘋如又說:「下午三點鐘,他跟日本人在虹口有個約會,我想二點鐘總要走了,就是這時候吧。」
「好的,我們二點鐘開始埋伏。」陳寶驊問:「那天妳穿什麼衣服?目標要顯著。」
最顯著當然是紅色;鄭蘋如想了一下說:「我那件紫貂的披氅,你不是見過的?」
「對,對,好!」
她那件紫貂的披氅,紅呢裡子,兩面可穿,如果將裡子當面子,紫貂出鋒,更為漂亮。那天當然這樣穿法。
「還有什麼話,你此刻都交代我。」鄭蘋如說:「丁默?的疑心病很重,我們今天見了面,一直到動手,不必再聯絡。」
「對,我們再把細節對一遍。最要緊的是,妳要跟他保持相當距離,免得妳受誤傷。」
「那末,你們是決定他一下車就動手呢,還是等他出來再打?」
「這要看情形。」陳寶驊想了一會說:「我想這樣,等你們出來,走到路中間,妳說妳有皮包忘了拿,回身進皮貨店,那時候我們再動手,就萬無一失了。」
「好,準定這樣。」鄭蘋如問:「事後呢?我回家?」
「不要回家,到卡德路來集合,看情形再研究。」
「我也覺得不回家比較好。」
接著又將重要步驟重新談了一遍,直到毫無疑問,鄭蘋如方始告辭。陳寶驊隨即召集主要助手,分頭部署;最重要的當然是通知張太太。
哪知張太太變卦了!「陳先生,我實在很抱歉。我正要來告訴你,為這件事,我跟我先生昨天晚上吵了一夜。他罵我自己找死,一定不准我那樣做。」張太太一臉的懊惱,「我先生的脾氣很倔的!怎麼辦呢?」
陳寶驊倒抽一口冷氣,只望著張太太發楞,好半天講不出話。
「我能不能跟張先生談一談?」
「談不通的。」張太太搖搖頭。
「這──?」陳寶驊不斷地吸氣,心亂如麻,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「這樣,陳先生,」張太太面現堅毅之色,「我把孩子借給你。你們總有女同志吧?」
聽得這話,陳寶驊略為寬慰了些;不管怎麼樣,問題算是解決了一半,還有一半,趁早去找路子。
「張太太,我不能讓你們夫婦失和,不過,我要冒昧問一句:到時候,會不會張先生又反對?」
「反對我把孩子借給你?」
「是啊!」
「不會,」張太太說:「我先生也不是不愛國,他認為這件事說來容易做來難,到時候我會『上場昏』,出了事,反而害了大家。孩子不懂事,就談不到『上場昏』,他為什麼反對?如果他這樣子不講理,我跟他離婚。」
說得這樣斬釘截鐵,而且道理很透徹,陳寶驊相信不至於再變卦,點點頭表示諒解。
「最好請你們的女同志早點來,我好告訴她,萬一孩子哭了,怎麼哄他。」
「好,好!我明天就讓她來。」
口中這樣答應,其實女同志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?回去找到周啟範一說,大家都傷腦筋了。
「只好再去找。」
一直拖到動手當天上午,還沒有找到「勇婦」;周啟範開口了:「我看不能找太太們。有家有業,有丈夫,有兒女,就是找到了,或許臨時顧慮太多,也會『上場昏』。愛國的女學生很多,說不定倒有哪位小姐見義勇為。」
「啊!『一言提醒夢中人』。」陳寶驊說:「一心只想為孩子找個媽,所以只在太太們頭上動腦筋,鑽入牛角尖了。」
說完,掉頭就走。他想到一位王小姐,二十八歲尚未結婚,因為眼界很高,不同流俗,平時議論世局,侃侃而談,充滿了正義感,像這樣的事,她一定願意合作。
趕到王家一問,說王小姐到浦東同鄉會看畫展去了,於是原車到浦東同鄉會,人群中一個一個看過去,查無蹤跡,復又趕到王家,仍未回來。王太太說,她女兒曾提到一部《萬世師表》的電影,得過金像獎,在大光明上映時錯過未看,這兩天重映不能再錯過機會,可能去看早場了。
一聽這話,陳寶驊趕緊找報紙查電影廣告,《萬世師表》是在一家光陸戲院上映,於是趕到博物院路光陸戲院,要求打燈片找王小姐。
「快散場了!你先生等一等好了。」
「不!」陳寶驊說:「還是要打。」
話剛完,領位小姐已經在拉門簾了,「是不是?」那人說道:「散場了。」
這一下,陳寶驊抓瞎了,戲院的太平門好幾個,不知王小姐是從哪個門出來?想一想,只好到對面行人道上,視界較廣,才有希望找到。
這時已經十二點半了,離約定的時刻只有兩個鐘頭,要到南市拿槍,再轉到卡德路去分配,時間非常緊迫,一分一秒都耽誤不得,可是能不能遇到王小姐,毫無把握,所以心裡一陣陣發緊,急得渾身冷汗直冒。
人都散完了,怎麼辦?陳寶驊心想,唯一的辦法,是先打一個電話到王家,關照王太太,如果王小姐回來了,請她千萬等候。主意打定了,抬眼一望,旁邊就是一家煙紙店可以借電話。陳寶驊便上前先買一包煙,然後問道:「請問電話在哪裡,我借打一個。」
「喏!那面。」
往「那面」一望,陳寶驊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,正是王小姐剛伸手去摘話筒。
「走,走!王小姐,眾裡尋妳千百度,得來全不費工夫!」他拉了她就走。
「陳先生,」王小姐問他:「什麼事?」
「我們上車再說。」
坐上三輪車,直奔南市。車上耳鬢廝磨,低聲密語,旁人只道一雙好親熱的情侶,卻不知談的是鐵血鋤奸的義舉。
果然,陳寶驊這一次是找對人了,王小姐在聽他的話時,態度顯得非常沉著;聽他講完,問一句:「你為什麼早不來找我?」
「是啊!我也在懊惱。」陳寶驊說:「因為有吃奶的孩子,所以我只想到年輕的媽媽,沒有想到小姐。」
「時間很侷促,不要誤事才好。」王小姐又說:「早知是這麼要緊的事,應該坐出租汽車。」
「也快到了。」陳寶驊又說:「王小姐,妳對抱孩子不外行吧?」
「我小弟是我抱大的。」
「那好!真正找對人了。」
四個人趕到現場,已經二點二十分,照約定的時間來說,可能晚了,但也可能不晚,因為約定的時間是二點到二點半,但願鄭蘋如跟丁默?遲到。
西伯利亞皮貨公司對面的大華路口,倒是停了好幾輛汽車,卻不知那一輛是丁默?。事先問過鄭蘋如,汽車的牌子、顏色與「照會」號碼;鄭蘋如說他車子有好幾輛,牌子各種都有,顏色是最普通的黑色,至於「照會」號碼就更無法知道了;因為常常掉換,就是同一輛車子,上午是這個號碼,下午可能變成另一個了。
由於約定是事先等候,行動員只要看到紅呢披氅女郎所伴同的一個「癆病鬼」,就是要制裁的目標,所以事先不知道坐那一輛汽車也不要緊。此時則不免徬徨,原計劃似乎也行不通了,因為不知道應該守住哪輛汽車。
十分鐘很快地消逝,為頭的老蔡轉身向大家看了一下先用眼色示意,再拗一拗嘴,於是四個人都到了西伯利亞皮貨公司,一面兩個,悄悄守候。
到底來了沒有呢?跟老蔡在一起的小朱,裝做瀏覽櫥窗中的樣品,沿著大玻璃窗從東往西走了一遍,卻以玻璃反光,一時無法看得清楚,於是由西往東,又看了一遍。
這一遍看壞了。他在明處,丁默?是在暗處,見此光景,心知不妙。本來照他們的工作經驗來說,如果到了一個臨時起意要去的地方,逗留時間不超過半小時,是不會有危險的,如今可能要出意外。
想到這裡,當機立斷,不肯做甕中之鱉,他很快地掏出二百美金,向正在跟店員研究灰背固好、豹皮也不壞,拿不定主意的鄭蘋如說:「挑好了,妳先付他二百美金的定洋。」
鄭蘋如不懂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,正想發問,只見丁默?已拔步衝了出去。等在外面的四個行動員心目中只有紅呢披氅的女郎,一時不曾留意,等發覺此人行色倉皇,方始省悟,可是丁默?已經坐上他的裝有防彈玻璃的汽車了。及至行動人員發覺,自然對準目標追擊,一時槍彈橫飛,行人四竄,只聽緊急煞車輪胎擦地擠出來的獰厲之聲不斷;丁默?的汽車著了好幾槍,但子彈是否打穿了玻璃或車身到了丁默?身上,卻無從判斷。
這時的鄭蘋如,自然成了西伯利亞皮貨公司中顧客和店員視線所集中的目標。
「小姐,」有個經理模樣的人開口問她:「陪妳來的哪位先生是什麼人?」
鄭蘋如一驚,遲疑未答之際,只聽警笛狂鳴;這下提醒了她,如果巡捕一到,自己就脫不得身,還不趕快溜走?於是她連丁默?丟在茶几上的二百美金都顧不得取,隨手拿起披氅,交代一句:「明天我再來看。」說完,往外急走,同時將披氅翻個面穿在身上。一到了行人道上,極力自持,擺出很從容的態度,穿過馬路,到卡德路的機關聚會。
到得樓上一看,除了陳寶驊,都是陌生人,她便不開口;陳寶驊也不招呼,低聲向那班陌生人說了幾句,將他們送走,才坐在鄭蘋如旁邊,苦笑著說:「為山九仞,功虧一簣。」
「我不懂,怎麼會讓他逃掉的呢?」
「唉,意料不到的事!找到人把槍送來,已經晚了。」陳寶驊說:「我亦不懂,他何以會突然發覺?」
「誰知道呢?」鄭蘋如恨恨地說:「我實在不大甘心。」
「蘋如,」陳寶華不勝歉疚,「這件事當然是我策劃不周。妳的責任完全盡到了,雖沒有成功,仍舊是妳的功勞最大。」
「勞而無功!」鄭蘋如很率直地說:「我要的是成功。我現在就回家,他可能會打電話來。」
「妳預備怎麼跟他說?」
「我裝做完全不知道,他不會疑心到我身上的。」
「怎麼不會?一定會。」
「我不相信。」鄭蘋如說:「不管怎麼樣,我總不能不回家,他疑心,也只好讓他疑心了。」
「那末,」陳寶驊說:「妳這幾天要小心,沒有事少出門。」
「我知道,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。」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