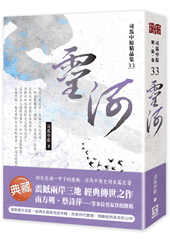
靈河的名字很美,但靈河實際上並不是一條美麗的河。由於上游的水源和水量很不固定,它的河岸彎曲成許多鋸齒形,當它消瘦時,它是和緩清澄的,它在暴怒的時刻,灰沌沌的含沙的激流,像是一條張牙舞爪的巨龍,直撲而下,彷彿要撕裂荒野,吞噬人畜。而在乾旱高亢的原野上,流水總是有助於萬物滋長的。因而,榛莽在這埋蔓延,林木在兩岸密舉,野蘆野草,綠火燎天,各種獵物,包括飛禽、走獸和水族,都跟著衍繁,而靠水維生的人們為了存活,也逐漸的結聚成村,繁衍成族,並且逐漸適應了依傍著這條蠻野的河川而生活了。
在這種偏僻的荒蠻裏,天是荒的,地是野的,連石塊都是多稜多角的,人們受了野稜稜的風物的感染,不用說也充滿了那種原始的野性,它剛健、正直、暴躁、單純兼而有之,但它也像激流一般的渾沌,在人們原始的心胸裏,由於缺乏文明的教育,在他們遇著紛繁複雜的事象,超越過他們能夠解釋的範圍時,他們就迷茫起來,僅能靠著荒謬的傳說,靠著沉默的自然面貌給他們以啟悟。
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裏,人,生下來,總要朝前活下去的,這就像山裏洪水積蓄到飽和時,要一路衝撞出來,尋覓它本身的出路一樣,它可以彎曲,可以迂迴,可以形成不同的式樣,但沒有任何力量,可以阻遏它朝前莽莽的奔流。生命和流水相同,環境,際遇,可以從表面上改變它的生活型式,那只是表面上的變易,不管人生的際遇是平坦的,坎坷的,哀傷的,憤怒的,或是充滿欣悅的,但它的生存的本質,卻從沒有更變過。
什麼是原始?什麼是文明?人們朝前活下去,永遠都在摸索當中,歷史所顯示的過程,只是人類遺留下來的摸索的痕跡罷了,靈河這樣的一條河,從古遠時日就這樣的奔流著,若干世代的,在靈河兩岸存活的人們,都在它的奔流中歸入墳墓,而它仍然流著,在後世人們的眼裏,自然也成為這一角荒天野地上的歷史的象徵,和一般有記載的文明歷史不同之處,是它不需經過史家的代言,只能讓人在天和地的靜默中,直接獲得靈性的參悟,因而,他們的摸索,也很夠艱難。他們的生活型態,正和混沌初開的圖騰社族一樣。
最先被人們一致認定的靈河這個名字,是附屬於一項古老的但仍可以證印的傳說。據說在很久很久之前,靈河還只是一條沒有名字的河川,靈河兩岸,也是野曠無人的荒地,有兩個帶著家小逃荒的漢子,挑著逃荒擔子,一路摸到這條河的岸邊來,一個姓荊,一個姓葉,他們一路逃荒,互相幫助,相處得頗為和洽,兩人都有意思結拜為異姓兄弟,問詢起來,姓荊的年齡較長,便稱為老大,姓葉的年齡略差幾歲,便成了老二,他們插草為香,拜了兄弟之後,便打算在這塊荒野地上安家落戶,搭起窩棚來從事開墾。
開墾要是合在一道兒開,固然在工作上有幫手,但開出來的田地算誰的呢?儘管荊大葉二倆人情同手足,彼此可以不分家,但傳到日後兒孫手上,那就扯不清了,倆人,有了這一層顧慮,便指河為界,荊老大帶著家小,住在河的東岸,葉老二帶著家小,住在河的西岸。
兩人沿河察看過,靈河兩岸的荒地上,全是石筍、石稜,和大大小小的石塊,土地不肥還不講,耕種時,連犁尖部很難插下土去,只有在河中段打彎的地方,現出一塊數里寬長,由流水沖積起來的大荒灘,灘地是細粒黃沙淤積而起,灘上樹林濃覆,蒿草叢生,多的是紅狐、野兔、黃鼠狼和值錢的水獺,既能墾田播種,又是一塊自然的好獵場,他們便各自選了荒灘對面安頓下來了。
那個夏天的夜晚,晴朗的夜空裏,星圖繁密,荊葉兩家人,各自在宅前的砂石場上歇涼,忽然看見天頂上起了流星,那顆流星曳著一串長長的、亮灼灼的光尾,在夜空裏劃了一道眩目的斜弧,直掛下來。
照理說,夏季星圖繁密,在乾亢的大氣裏看見劃空而降的流星,是極尋常的事情,有時逢著流星雨,一剎間能見到天頂四周,此起彼落,紛繁如雨的光弧鼠竄。但這顆流星卻不一樣,它筆直的彷彿朝人的頭頂上落了下來,銀白的光弧越變越大,幻成一片橘色的流火,不甚解事的孩子們都驚惶又喜悅的大聲喊叫著:
「看啊,看啊!斗大的流星燒天啦!」
「它要落到這裏啦!」
喊著喊著的,流星真的落了過來,他們只聽見轟然一聲巨響,使河兩岸的土地都興起輕微的震顫,那塊熔紅了的巨石,果然落到河的西岸邊的荒草地上了,把沿河的荒草點燃起來,燒出一片紅毒毒的大火。
二天火熄後,兩家人都跑去看視那塊從天外落下來的殞石,它像一座房屋那樣的高大,形狀像一隻巨龜,通體光潔黝黑,看著很覺得怪異,因為它是天降的神石,不同於一般人世上的石頭。
荊老大和葉老二倆個,叼著煙桿蹲在那塊石頭面前計議著,兩個人都是沒讀過書進過塾的粗人,知識有限,荊老大認為殞石形狀像龜,龜和鶴是一般人意識裏長命百歲的動物,主壽考的,當然也是主吉祥的。葉老二點頭同意荊老大的看法,認為天下這麼廣闊,流星不朝旁的地方落,偏偏落在他們所擇定的落戶安家的地方,也許這是天落靈異,發為瑞徵,象徵著荊葉兩家人日後子孫興旺,繁衍綿延,既有這種好兆頭,就該豎起一塊石碑來紀念它,讓它接受兩家的香火供奉。
碑石就是這樣豎立起來的,荊老大和葉老二兩個人,跑到遠處去央託有學問的人,替那塊殞石取名為神龜石,替那條荒蕩的河川取名為靈河,意指這宗落石河濱的神蹟,充滿了天降的靈異。
這傳說聽來是荒緲的,但住在靈河兩岸的人們,並不認為它有任何荒緲之處,因為那塊神龜石和石前豎立的石碑,都遺留在河岸的野路邊,足見那是真實的。
只是時間輾轉過去,離開初的日子很久遠了,據說靈河落石之後不久,便有更多的人紛紛匯聚到這裏開荒行獵,如今河的兩岸炊煙不絕,星羅棋布的屯子有好多處,人煙雖不算繁密,但跟當初只有兩家人的光景,已經大下相同了。
河東的荊家屯子和河西的葉家屯子,隔著荒灘,遙遙相對著,每個屯子都有好幾百戶人家,繁盛的光景不亞於遠處的集市,靈河上游近山口,有一處石家老莊,那兒的居民真的是靠山吃山,他們開設鋸木廠,石灰窯,開採條石和石板,有一部分人家雕鑿磨盤,舂舀,碾場舊的石碌碡,靠了石匠手藝,販賣成品維生,下面一些的楊家莊,多半是些獵戶人家,有的追狼,有的逐兔,有的獵取水獺,或是硝製皮毛出售牟利,在荊葉兩座屯子附近,更有不少的散戶人家,他們一樣是就地取材,從事生產,有的種植白柳和觀音柳,編織籮筐、提籃、簸箕等類的物件,有的採取大片的野蘆桿,編成蘆蓆批售;有些製網製獵罟(按:張在陸地上獵獸的巨網通稱為罟。),有些從事漁撈,也有些開闢渡口,結紮成巨型木筏,在靈河上擺渡,接引來往通行的渡客。
沿著渡口附近,也有了麇居的商戶,他們以當地的居民,過往的行商,麇集的獵戶,以及收取皮毛的商賈為對象,開設吃食鋪、茶館、或是做販賣日用品,各式雜貨的生意,像煙絲、燈草、草鞋、麻製車攀、油鹽、碗碟、布疋之類的貨品,都是銷行極旺的,另有一些行業也很應時,諸如搖鼓貨郎、獸醫,從事修蹄釘掌的,看相算命的,巫童和巫婆,僧道之屬的人物,也都點綴其間,彷彿是藥中的甘草。
無論是世代安居在這裏的老戶,還是新移屯來此的人們,無論他們從事哪類行業,但凡住在靈河兩岸的人,都熟知殞星落地的傳說,也都尊重那塊黝黑的神龜石,奉以香火,並且把神石落地的那一天,定為節日,全體居民們都會自動的聚集起來,舉行盛大的祭典。他們是藉著這個隆重的祀祭儀式,表示出他們對於上天的感恩。
大體說來,這裏的人們,一向習慣用荒蠻的野地和傳說來教養他們的子女,河西岸的渡口邊,小賣鋪裏的嬌靈,就是這樣長大的。
嬌靈是個女娃兒,自小長到十多歲,不知道胭脂花粉像什麼樣子?走出門去,瞇起眼迎著風,用風沙洗臉,把她的臉都洗粗洗黑了,除了腦後拖一條壓住脊樑的辮子,跑起來兩邊悠幌,她跟男孩沒有兩樣。
小賣鋪的茅屋蓋成丁字形,座落在河崖的丘頂上,一面朝向渡口,一面臨著河。房舍那樣低矮,簷口常會打著人頭,當然都是高個子男人首當其衝,所以,她每遇著高大的客人進店,就大聲嚷叫著:
「當心碰著頭!」
誰知有些人偏就那麼冒失,走起路來,急急衝衝的朝前撞,彷彿要爭著看什麼熱鬧似的。她一聲還沒喊完,熱鬧就來了,對方已經一頭撞在簷口上,落了一頭草屑,卻讓她搖鈴般的笑著,白撿了一場熱鬧瞧。
有些漢子竟然是那樣粗心又健忘,進門撞了一回,出去時總該記得彎彎腰了罷?嘿,竟然又撞上了門框,這一回門框是硬的,腦門撞得咚咚響,再揉也會腫起一個大疙瘩,嬌靈的笑聲可會惹出被撞的漢子發火了,叱喝說:
「笑?什麼好笑?慣會幸災樂禍的,丫頭片子,小黃毛!只怪妳家屋子蓋得太矮了,有什麼法子叫人不撞著頭,妳說說看?」
「有啊!」嬌靈說:「找把鋸子,把你的腿鋸短一截,包你不會再撞著門框。」
「嬌靈,不許跟客人開這種鬼精靈的玩笑,」這時刻,拖著一把白鬍子的爺爺就會捏著長長的煙桿出來解圍了,他笑得擠出一臉桃核似的皺紋,指著被撞腫額頭的客人說:「人家是福大命大,個頭也大,不慣進出低門矮戶的人家,我老頭兒雖不是看相的,也敢打睹,人家這一輩子,決不會窮困得住進寒窯的。」
爺爺嘴裏的寒窯,只是習慣上的比方,靈河岸不是西北的某些省分,也沒誰真的住過寒窯,只不過唱野戲的經常唱到薛平貴回窯,這兒的人們都曉得窯屋是貧窮人居住的地方。爺爺這麼一說,被撞的人可樂了,臉紅紅的笑著,謙遜的說:
「老爹您真會比方,相府千金住的地方,咱們哪會有那種命咧?只怕想住還住不進去呢!」
客人一走,嬌靈就歪起頭來問:「爺爺,薛平貴回窯,是不是也像剛剛出去那個人一樣,額頭上撞出一個大疙瘩?」
「我怎麼會知道?」爺爺叭噠叭噠的吸著煙說:「就算真有,戲上也不會演出來的!」
「應該加一段,怪笑人的。」
可是爺爺不愛笑,一臉的皺紋,彷彿都是常年悶聲悶氣鬱出來的,由此測得出,平時爺爺當著客人的面,捏著長煙桿,打出響亮的哈哈,都是裝出來使出來的,他心裏並不真的想笑,要不然,為什麼等客人一走,他那張臉立刻就冷了下來?
怕看爺爺悶聲不響的噴得一屋子煙霧,嬌靈就會拔腿跑到屋外去,屋外的天地是開朗遼闊的,荒路邊有一排楊柳椏樹,樹邊留著許多野炊用的糊鍋洞,樹下橫著一排獨木挖成的驢槽。嬌靈總覺得大人們硬把那東西叫「驢」槽,實在太霸道了一點,因為她明明看過那兒也拴過騾子和馬,有時也拴羊和牛隻。
實在的,嬌靈看不慣有幾匹長耳朵的驢子,牠們太不老實,放著槽裏拌妥的麵粉草料不吃,偏要伸長頸子,吱起大牙去啃樹皮,再讓牠們那樣亂啃,楊椏就會被牠們啃枯了!所以她不放心,常要跑出來看看,有沒有那種饞嘴的騷驢偷啃她家的楊椏樹?
這兒過路的客人不多,驢槽經常空著,她便安心的坐在驢槽上,悠蕩著小腿,哼哼唱唱的望著遠方,靈河在流著,灰沌沌的流水波漾波漾的,從不知名遙遠處流過來,又流向不知名的遙遠……
朝下游望過去,平野又渾圓又遼闊,到處鋪著拳大的秒石稜兒,灰白灰白的,像無數大鵝蛋。流水那邊是荒灘,水蘆和旱蘆連成一片,水鳥和陸地上的鳥蟲飛到一起,成天吱吱喳喳的在爭吵著。灘上的林叢密得很,樹梢擠著樹梢,像一柄倒豎的梳齒,獵戶們常搭何禿子的木筏,到灘上去圍獵,隔著河,她當然看不見獵物,但她常常記起年老的爺爺講給她聽的,那些使人神往的,行獵的故事。
爺爺在家時,嬌靈的日子是好的,爺爺喜歡在晚飯時喝上幾盅酒,讓酒暈染紅他蒼老的臉,和他滿頭稀疏的白髮相襯映。帶著幾分酒意的爺爺閒著沒事了,打著飽嗝,拖一條長板凳在門前坐著,長凳的一端,擺著小茶壺和一隻裝煙絲的小扁盒,他總是先捏著煙絲,裝滿一袋煙,打火吸著,一面用蒼老僵涼的嗓子,對她講些奇怪的故事。
其中有一個很恐怖的,爺爺偏偏講了兩三回,他說,早年裏,荊家屯子和這邊的葉家屯子一直相處得很和睦,互婚互市,都算是老親世誼,那年河西葉家屯子族主的第三個兒子葉爾昌,帶著幾捆貴重的皮毛到遠處去販賣,賣得一筆好價錢回程,在經過河東荊家屯子東南角黑松林子的時刻,被人用悶棍打殺了,搜盡了錢財,把葉爾昌的屍體掩埋在黑松林子當中。
葉家人怎會曉得?成天伸長脖子盼望,一等也不來,二等也不到,把眼珠子都急紅了,也沒看見葉爾昌的影子。葉老爹提心吊膽怕出意外,特別差出大兒子葉爾靖,率同幾個槍丁,騎著牲口,乘木筏過河,順著葉爾昌走過的那條道路一路追查過去,路上沒有發現,他們一直追查到縣城裏面。
年富力強的葉爾靖有過多次出遠門的經驗,辦起事來精明幹練,葉家屯子的人都稱他做小族主,他一到縣裏,就查出他家老三落宿在老茂昌客棧,租的是後套房,前後住了五宿。
葉爾靖問店家:「他可帶的皮貨?」
店家想了想說:「不錯,他騎的是一匹大青騾子,帶有兩大捆皮貨,聽說是賣給姓海的大皮毛商了,收的是現大洋,雙馬子揣得鼓鼓囊囊的,……他回程那天,還有人跟他同路呢!我記得他要小二替他牽牲口時說過:有個伴兒也好,錢帶得太多,一個趕路,真怕出岔子。」
「誰跟他同路?您還記得不?」
「看相的呂鐵嘴,」店家說:「說起來您認得他,每年冬頭上,靈河岸開設野集售貨,他常去那兒設相攤子,替人看相。他們同路同到哪兒為止,我就不清楚了,至少,那天早上,倆人是在這裏同時起腳的。」
葉爾靖在城裏找不到呂鐵嘴,多方向人打聽,說是呂鐵嘴若沒去靈河岸,就是去大龍家寨去了,大龍家寨在靈河東七十五里地,除了縣城之外,它算是四鄉最熱鬧的集鎮。
葉爾靖心急如火,牲口沒鬆肚帶,僅僅略加些草料,就連夜趕奔大龍家寨,很容易把呂鐵嘴找到了,問起那天的情形,呂鐵嘴顯出極驚詫的神色說:
「怎麼?葉老三他還沒到家?那可就怪透了,當天我和他一道兒動身是沒錯的,他身上帶了不少現大洋,我也知道,在路上,我還要他留意點兒,銀錢帶多了,一個人趕長路不甚方便,萬一遇著歹毒的人,就不好辦了…… 葉老三根本不理會,他拍拍驢袋囊,說他帶的有短柄火銃,足夠防身的。我們是在晌午前分首的,當時走到三岔路口,我朝東來大龍家寨,他朝西北奔靈河,三岔路口老孟在那兒擺花生攤子,我們坐下歇了一會,臨走時,各人都買了兩捧花生。不信您去問老孟,就知道了,我奇怪的是他沒回到家裏,又會到哪兒去了呢?」
「呂鐵嘴,你說的都是實在話?」
「囉,小族主,」呂鐵嘴苦笑說,「我是在跟什麼人回話?我敢講半個字假話?我是走江湖混飯吃的人,日後還要到靈河兩岸去做生意呢,老孟他會替我做證的。」
「好!我這就去找老孟,問個清楚。」葉爾靖說:「我家老三一天沒回去,你就一天脫不了干係。」
葉爾靖離開大龍家寨時,和同行的幾個槍丁計議過,大家都覺得呂鐵嘴是個瘦得皮包骨頭的傢伙,憑葉爾昌的骨架和身手,一拳能把他打飛兩三丈遠,再說,這多年來,呂鐵嘴常跑靈河岸,有根有絆的一張熟面孔,他也不會見財起意,勾結歹人幹這種劫奪的案子。
對呂鐵嘴最有利的,是三岔路口擺花生攤的老孟,力證當天晌午前,他和葉爾昌確曾在那裏坐了一陣,拴妥牲口,喝了茶水,吃了些炒花生,然後分路的。老孟自己種花生,是個和善誠實的老人家,說話有一句是一句,從來不打謊的。那麼,葉爾昌一定是在三岔路口朝西北,一直到靈河岸邊這段路上失蹤的了。
他們朝回查,查到黑松林子那裏,看見許多烏鴉在林梢飛旋下去,哇哇的噪叫,葉爾靖念頭一轉動了疑,進林子去細察,果然找到一隻鞋子,他一眼認出是他兄弟葉爾昌穿的,一個槍丁發現附近有一堆軟塌塌的新土,他們刨著試試,誰知刨下去沒幾尺,就把葉爾昌的屍首刨出來了。他的臉孔發紫腫大,眉目還算清楚,致命的傷痕是在後腦上面,被人用鈍器打裂了,大青騾子、雙馬子和銀洋全都不見了。
「這宗無頭命案,是許多年來頭一宗。」爺爺嗨嘆著:「打那時起始,靈河就不太平了。葉家屯子的人,認為命案發生的地點,是在荊家屯子的地面上,十有八九是姓荊一族裏的敗類幹的,荊家聽著這種風傳,大為不滿,認為事無憑證,葉家屯的人怎敢血口噴人?……說著說著的,這事業已過去十年了,兩個屯子都還記恨著,而命案也曾訪報過官,葉爾靖也不斷在暗中查過,直到如今還沒有絲毫頭緒,看樣子,葉爾昌算是埋冤啦……」
嬌靈不喜歡聽這個恐怖的故事,爺爺偏偏講了。
爺爺還講了許多和這種命案有關的傳言,據說鄉野上有一種歹人,練就一雙賊眼,即使過路的客商行旅所帶的銀錢不露白,他們單憑一雙眼,遠遠的看上一看,就能知道對方身上有沒有貴重的財物。
「那些歹人判斷客商行旅所攜的財物怎麼看呢?」爺爺說:「首先是看他走路的樣子,假如把頭伸在腳尖前面,一股垂頊喪氣的樣子,這個人即使不是乞丐,定歸是窮愁潦倒的人物,假如腳踢得像馬蹄,一步就是一步,腳尖總超過人的鼻尖,這個人多半是腰懷多金,正合上俗話形容的:腰裏揣著錢鈔,走路胸脯都挺得高些兒!……這只是一般的看法,靈不靈不定十分準確,那些歹人還有大訣竅,那就是看來腳下飛起的沙煙,……如果是個沒錢的,沙煙最多飛昇到腰際就不再上騰了,如果他有些錢,沙煙可以昇到肩胛骨那麼高,如果他懷揣金元寶呢?嘿,沙煙就會飛到他的頭頂上,盤結成一朵朵的黃雲了。」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