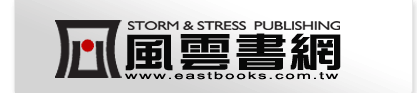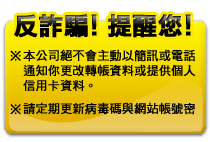大歷史‧大文章(中古篇)──【大歷史的脈動與輝煌】(起於唐代,迄於明代)

《史通》自序
劉知幾
劉知幾(六六一—七二一),字子玄,唐朝彭城(今江蘇徐州)人,進士及第,於武后時遷至鳳閣舍人,兼修國史,開元年間曾官至左散騎常侍。劉氏熟讀《春秋》,長於史事,著有《史通》,標舉史書之法,開我國討論史學之先河。
背景
唐宋以來,史學評論的風氣日益興盛,然而歷來舊史叢脞複雜,異說謬誤混淆,直至唐代劉知幾撰著《史通》二十卷,始得以整理釐清而樹立規模。
劉氏久居史官,博覽典籍,曾屢次參加當時政府修史工作,因感無法發揮己見,所以「私撰《史通》以見其志」,於唐中宗景龍四年(七一○)完成《史通》全書。
《史通》全書五十二篇,《體統》《紕繆》《弛張》三篇已亡伕,今存四十九篇,計內篇三十六,外篇十三。大抵內篇論史家體例,外篇述史籍源流。而以全書來說,關於研究法者計三十四篇,其中論原委者三篇,論體例者十七篇,論考證者十三篇,論方法者一篇;又有關於編纂法者計十四篇,其中論方法者九篇,論才能者二篇,論內容者三篇。另有自敘一篇,只言本書旨趣。
唐以前史籍雖多,大致出於模仿,劉氏歸納為六家。而以編年史、紀傳史為史家正體,稱為「正史」,其他旁流稱為「雜著」。不僅分析其流派,並對筆記、方志、家譜、都邑等記載同等重視。
劉氏主張以斷代方式為史書體例,尤其注意史料的真實性,且勤於綜合,勇於懷疑,並反對盲目仿古,肯定史書雖載往事,但應使用當代語言文字與通俗詞句從事編述工作,此點對於後世具有重大啟示作用。
影響
《史通》為我國最初的史學理論書,亦為我國著名史學評論著作,在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。劉氏於《書志篇》中強調都邑、氏族、方物三志的重要,日後宋代鄭樵《通志》中有《氏族略》《都邑略》,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中又別立《土貢考》,皆遙承劉氏建議而增闢。
此外,劉氏為便於評論古今史籍,往往將漢魏六朝、隋與初唐許多史書一再加以引述,現在諸書皆亡佚,但就其中所引資料,可以瞭解諸舊史中若干片段,所以《史通》在史料學方面也有值得重視的價值。
原文
長安二年,余以著作佐郎,兼修國史。尋遷左史於門下,撰起居注,會轉中書舍人,暫停史任,俄兼領其職。今上即位,除著作郎、太子中允、率更令,其修史皆如故。又屬大駕還京,以留後。在都無幾,驛征入京,專知史事,仍遷秘書少監。
自惟歷事二主,從官兩京,遍居司籍之曹,久處載言之職。昔馬融三入東觀,漢代稱榮;張華再典史官,晉朝稱羨。嗟予小子,兼而有之。是用職司,其憂不遑啟處。
嘗以載削餘暇,商榷史篇。下筆不休,遂盈筐篋,於是區分類聚,編而次之。昔漢世諸儒,集論經傳,定之於白虎閣,因名曰《白虎通》。予既在史館,而成此書,故便以《史通》為目,且漢求司馬遷後,封為史通子。是知史之稱通,其來自久,博采眾議,爰定茲名。凡為廿卷,列之如左,合若干言。於時歲次庚戌,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。
《史通》
譯文
武后長安二年(七○二),我擔任著作佐郎的官職,並且兼任編修國史的工作,沒多久就升到門下省,擔當左史的職位,纂修皇帝的起居注,後來因為轉任中書舍人,曾暫時停止史官的工作,沒多久即又恢復原職。當今皇上就位後,派我擔任著作郎及太子中允、率更令的職位,像以前一樣編修史事。後來皇上到京城,我在洛陽沒多久也被徵召回到長安,專掌史官的職位,也擔任秘書少監。
我常想,我曾經在武后和今上兩位國君之下做事,在長安、洛陽兩京任官,掌管過各種典籍,又長久擔任史官的職責。當年馬融曾經三次到洛陽東觀任史官,漢朝人人視為榮耀;張華也一再執掌史官的職位,讓晉朝大家稱羨不已。而我雖不才,他們倆的職位,竟然都有緣擔任。為了擔任史官,我終日戰戰兢兢,唯恐不能把事情做好。
我曾經在公餘之閒暇,討論史篇,一下筆就不能甘休,因而草稿堆積了好多,於是就按照分類,加以編排。當年漢朝一些儒生為解決經傳的問題,聚集在白虎觀加以討論,後來作了定案,因此就命名為《白虎通》。我既任職於史館,而完成了這本書,所以就把它喚作《史通》。況且漢朝曾經尋求司馬遷的後人,封為史通子,可知史書喚作史通,來源已經好久了。我因而依照往例,廣采眾議,也定此書名為《史通》。共有二十卷,詳列於左,總計文字若干。時在中宗景龍四年庚戌年(七一○)二月。
(周益忠、陳韻/編寫整理)